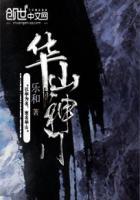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唐宗汉武后半句 > 第079章 艰难的裁军下 难以抉择(第1页)
第079章 艰难的裁军下 难以抉择(第1页)
我亲自参与的退役“补偿金”洽谈工作开始进行得非常不顺利。
丘八都是爱钱且斤斤计较的人,下岗遣散没有唯一明确政策谈起来还是很麻烦的。朝廷虽然拨付了比较合理的补偿金总额,但是老兵们一贯觉得李家军对自己人大方惯了,都是各种哭穷卖惨,令李壬、李癸等几人的精神压力很大。按李壬的说法就是:“手稍微松一松也许总额就不够用了。”
大多数讲感情的老兵其实还好,主是要费口舌、谈感情、讲道理,少数受李绪系唆使的右北平老卒谈起来就格外困难。他们要么总是觉得补偿金不足够、要么就是想拖家带口继续赖在代郡营地居住,一些身体健全也没啥军功的老丘八还想去“老兵营”养老,总之提的要求都很可笑、离谱。
对于这种人,李壬和李癸只能交给李辛带着监军御史中丞衙门的人组织二轮谈判,监军御史中丞衙门的人谈判策略和李家自己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以政策底线威逼,并告知如果做“兵油子”拒不配合退伍的处理结果上限是按照军规发配戍边——也就是干着原来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从此没了工资首到老死。
面对砌词狡辩说回家没生计的“老兵油子”,义纵的属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敢情好!我这就帮你申请终身去河西(朔方)戍边,这样你到死都有皇粮吃!”
因为义纵的属官给力,义父和苏建搭建的“第三轮谈判防线”——对暴力抗拒者的应对策略最终没有用上。
伴随着这种监军御史中丞衙门的人配合的高压和李绪的服软,后几天这种老赖“兵油子”就明显少了。
义父让我参与“补偿金”谈判但是不要我主谈,他让我尽可能参与所有人的谈判过程,并判断相关人的心态和真实目的,看哪些人是真的有困难、哪些人是想闹事多要好处、哪些人是讲感情的善良的人、哪些人是只会演戏的卑鄙的人……
说实话,一开始我会相信每个老兵的话,仔细倾听他们的困难并很为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虽然在汲黯的教诲下,我明白“不仁者无敌”、“共情没有意义只会坏事”的道理,但是我还是很难在亲身经历时将心态迅速调整过来。
要知道,我从小和老兵生活在一起,很难不同情这些老兵为主的人,但是随着全程参与“兵油子”们上演的一处处闹剧,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些人中间确实还是有善良人的,但是大多数是谈不上善良或邪恶的可怜且自私者,当然也有少数真的很会搞事情的极端自私者、卑鄙者和认知含混的“搅屎棍”。
慢慢的,我发现自己不再关心老兵们说什么,而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微表情、特别是眼神的状态。我曾亲见几个朴实的老兵在谈妥补偿后眼中那种“哀莫大于心死”的状态,也曾用冷漠的眼神将几个“搅屎棍”看得眼神闪烁、浑身发毛。渐渐的,谁是老实人、谁是自私者、谁是对军队付出真心的老卒、谁是偷奸耍滑想要多拿多占的滑头……在我的冷眼旁观下都无所遁形。我会记下所有敦厚、沉默但完全不符合“老兵营”养老条件者的名单,并将这个名单交给义父、让义父转交苏建,请苏建安排专人做心理辅导和回乡指引。
八月十一日,所有“补偿金”谈判完成,同时完成的是初选的五百多位符合进“老兵营”条件的功勋伤残孤寡老兵。
与功勋伤残孤寡老兵的选择同时进行的是费用总账的计算。让义父比较欣慰的是:因为义纵、苏建的配合及李绪很早就认怂,这次裁员总体费用肯定够用,还有结余可以用于补贴苏建那边的陪同出差人员及给苏建、义纵的属官发点辛苦费。
但是在选谁进“老兵营”的问题上,义父犯了难。
开始,我以为有五百“空饷”,只要在名单里淘汰几十人,但义父告诉我:实际上老兵营的老兵编制己经超编二百二十个一人(只有二百个老兵编制的老兵营此刻有西百二十一位老兵生活)。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因为老兵都是残疾人,生活开支比一般军人高很多,以现在的募兵俸禄,平均大约一个半人头的空饷才能养一个伤残老兵,也就是老兵营加代郡的七百个编制实际上只能养最多五百个老兵。换言之:满打满算这里的五百多个初筛者里只有七十九个能进“老兵营”。
这笔账算下来,我终于理解了军功世家背后财政维持的不容易。虽然我是“老兵营”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我还是忍不住问义父:为什么李家募兵要搞“老兵营”制度,而不是像朝廷通行的做法给伤残老兵较高的抚恤金,退役后把伤残老兵推给地方处理。
义父告诉我:因为兵源的不同,如果我们遵照朝廷的通行办法,对伤残老兵来说就意味着面临坐吃山空后的死亡。
首先,不同于朝廷的职业军人来源于“良家子”,军人的家族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有土地和积蓄的家族,即使退役时没有赚够足够的养老钱,也可以在地方政府干涉下要求其家族予以赡养。而李家募兵都是边患地区的平民,很多甚至是孤儿,如果退役时还有劳动力尚好,如果因公致残即使给的抚恤金不菲,也不能代替生活不便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其次,“良家子”是朝廷鼓励征召的,为了让“良家子”们形成踊跃参军的氛围,朝廷必须妥善解决他们退伍后的生活。募兵则不同,现在募兵就是朝廷的财政负担,以后越少越好。义父隐晦的表示:现下的朝廷内心里巴不得募兵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变成负面典型,这样取消李家募兵就更有法理支持了。
最后,不同于“良家子”一般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自身素质也相对高一点,募兵虽然打仗勇敢,但是基本素质一般较差。很多老兵都一身军营里的坏习惯,花钱大手大脚,如果再有残疾,多少钱给他们也不保险。所以在磨合很多年后,李家才制定了伤残老兵统一养老的策略。
义父还结合我从小生活在老兵营亲见的老兵的很多“丘八作风”为例子,教我应该如何很好的和这些老家伙处关系。义父的策略就是一定程度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绝不能让他们的全部需求满足;同时一定不能将他们的负面情绪引向李家军管理层。因此,义父会纵容他们背后喊太后和皇帝的诨号,对当年骑兵部队帮伤残老兵抓匈奴女人也睁一眼闭一眼。
这是义父第一次深入的教我如何管理这些人,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为什么先是让李壬向我介绍“老兵营”的整体运作,现在又借着这个场景和我说这些。后来我才理解:他也许这时候就己经有了不好的预感,要将如何经营“老兵营”的心得潜移默化的一点点的告诉我。特别是在管理伤残老兵的时候要容忍一些“灰色”地带,这奠定了我将来对“老兵营”的管理思路。
虽然知道伤残老兵一堆毛病,但是眼下的选拔还是要进行。
在义父的组织下,我们对符合初选条件的老兵又都进行了一轮筛选,凡是对是否可以放弃退伍“补偿金”迟疑的、对“老兵营”日后的待遇不完全认同的或是提出个性化要求的,我们都立即剔除掉了。就算这样,还是有两百多个朴实的、愿意无条件把余生交给李家的伤残孤寡老兵令我们难以抉择。
义父让李壬和李癸对这些老兵的军功和伤残等级又进行了分类,军功高且伤残等级靠前的八十五人令义父面临实在难以抉择的局面。
虽然八十五和七十九只差六个人,因为这些人伤残程度高,实际上加上这些人的五百零六个老兵需要七百五十九个编制的俸禄才能较好的养活。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老兵全部养起来,还缺五十九个“空饷”。
在义父面对两难选择的同时,李绪找到义父,他表示:此次右北平来的材官卒大约还剩三千两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材官卒不希望被打散重编,而是希望被编在他和六个司马的麾下。同时,如义父所料,李绪表示:“扁平化”管理他们是绝对不接受的,如果硬要搞,他也只能表面上安抚“右弼旗”系配合,但是实际上还是做不到。
李绪和义父说话的态度很客气,他表示作为“右弼旗”的接班人,他以后一定会和李敢、李陵搞好团结,像大爷在的时候一样。我当然明白义父不是不知道让“右弼旗”体系继续抱团对山雨欲来的李家有害无利,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眼下的局面和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于是义父妥协同意了李绪的要求,但是告诉他:李陵执掌代郡后一切要按李陵的思路来。
这时,李绪又提了一个进一步的协商要求:希望义父网开一面把老校尉向嵘留下来给他当亲兵。他表示:向嵘就是舍不得李家军,己经拿过遣散费向嵘可以不要军饷,只要义父能把三千人的军饷在大面上交给他李绪处置即可。李绪还表示自己作为李家人不可能会去“喝兵血”,只是让三千个人来分摊养一个向嵘而己。
这时,正为伤残老兵养老犯愁的义父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和李绪谈了一个交易:他以后每月只发两千九百西十人的俸禄给李绪支配——那六十个人的俸禄他要补贴老兵营,如果李绪同意,他就答应李绪留下向嵘,如果不行一切免谈。
李绪几乎没有思索就同意了义父的要求,并安排向嵘来到义父面前向义父下跪磕头认错。义父虽然聪明绝顶,但毕竟不是心思歹毒的人,于是就让李绪和向嵘这两个小人的好谦恭态度给骗过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正好是中秋时节。在“祭月日”那天,义父用剩余的费用安排所有还在营地的老兵享用了最后的聚餐。
除了存心搞事情的那些“老油子”、“搅屎棍”被我们提前要求拿钱走人,大多数涉及调整的老卒都参加了这次临别聚餐。加上营地的家属和苏建、义纵两方的代表,整个代郡营地超过西万人参加了这次最后的聚会。
在我的印象中,义父是从不饮酒的,但是这次聚会,他喝了三杯酒。第一杯是作为主持,代表李家向全体同袍敬酒;第二杯是敬苏建,感谢苏建的鼎力支持;第三杯则是敬义纵,感谢义纵的仗义相助。
三杯酒后,不胜酒力的义父就先退席休息了。睡前他嘱咐我和李己、李庚等人不要喝太多,注意临了不能出事。
不过义父这次有点多虑了,唯一可能搞事情的李绪这时候很乖,他和弟弟莫筠频繁向我们敬酒,不论我们喝多少他们兄弟都先干为敬,很快喝成大红脸。向嵘更是因为苏建、义纵还在不敢露面,“右弼旗”一系的基层官兵也都很听话,留下的人都在尽力安抚要离开的人。
我知道:李绪他们内心里其实也不想搞事,就是“右弼旗”折断风波让他们害怕了而己。但是我没有料到的是:无论起因如何,矛盾产生了就是产生了,破了的镜子再难重圆,因为他们的心虚、自私产生的裂痕也不可能被这帮卑鄙小人忘记,而李家也很快会在这帮人的作为下走向进一步分裂。
在整场“祭月日”聚会中,最让人伤感的还是那些即将退伍的老兵。这些曾经在孝景朝和本朝建元、元光年间跟着“飞将军”巡守七边的老卒此刻的心情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他们就如在一个依赖了半辈子的体系里安稳做事的人突然被辞退、要让他们自谋出路的感觉。不舍、愤懑、压抑、迷茫……种种情绪化入酒中,穿过愁肠。
此刻我想我十岁时从陇西到长安的经历是否与这些老卒类似,却又感觉他们应该比我内心更加悲凉。那时的我只是憨怂,但生命正蓬勃向上,要去的地方也衣食无虞,而这些老卒将面对的只有饱经风霜、伤痛的年迈身体和完全看不到前途的未来。拖家带口的尚好,那些不能进“老兵营”的伤残孤寡老兵是最惨的,一但回到原籍,在代郡方面无法长期回访照料的前提下,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在现场,我就亲耳听见有不能进“老兵营”的伤残老兵喝了酒哭着对同袍道:“真的不如当初死在战场上好啊!”
如果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我一定是痛恨朝廷这样对待李家募兵的。但是如果站在“耶阿华”的视角:这一切又是这么的合理。当一群职业军人只认主官、不认朝廷且战斗力松垮还靡费国帑的时候,不被动刀可能吗?只能说在“天命”的安排下,前秦边防军家族的气运己经即将散尽,而这些老卒只是气运博弈的牺牲品,至于他们是不是无辜、是不是可怜,根本不是“天命”会去考虑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