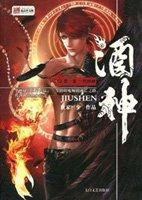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华夏英雄传原版 > 第四十三章 夏王遗孤(第3页)
第四十三章 夏王遗孤(第3页)
仿佛是为了将这绝望彻底钉入骨髓!帐外,由远而近,暴雷般密集而沉重的奔马蹄声猛然炸响!如同无数柄重锤带着毁灭的力量,疯狂地擂击在冻得铁硬的冻土地面上!蹄声如雷!首冲酋长大帐而来!
“娘——!!!”一声嘶哑得如同野兽临死前撕破喉咙、带着无尽恐惧和狂怒决绝的年轻咆哮,硬生生撞开呼啸的风声与厚厚毡帐的阻碍,如同血淋淋的楔子狠狠钉了进来!
砰!
帐帘被一股更为狂暴的力量猛地扯开!
一道身影裹挟着冻原上最刺骨的寒流与铺天盖地的绝望风雪,如同离弦之箭撞入!少康!他身上的旧皮袄破了几处大口子,露出底下同样划破的里衣,汗水与融化的雪水混合着泥浆将他额前的黑发紧贴在苍白的皮肤上,脸上交织着剧烈奔行后的、病态的潮红和一种源自血脉最深处的死灰般惊惶!他的目光只在大帐内扫了一眼——如同雕像般绝望的长老,捧着断腕的酋长,以及僵坐在毡垫上、生机仿佛被瞬间抽干、胸前衣襟渗出刺目暗红的母亲——那死灰般的惊惶瞬间被点燃,炸裂成足以焚毁一切的野火!
他一步踏碎了大帐内冻结的空气!脚下的羊毛毡毯被巨大的力道掀起涟漪!身体带着狂风扑至后缗面前!双膝如同沉重的石夯,狠狠砸在冰冷坚硬的泥土地面,发出令人心头俱震的闷响!
“走!”喉咙里爆出的己经不是人声,而是被绞碎内脏后、从齿缝里挤出的、混杂着血腥气的绝望嘶吼!那双年轻却被生活刻上风霜的眼睛此刻完全被野兽般的狂躁吞没,带着焚毁一切的疯狂!他一手死死抓住母亲那枯槁如同朽木般的冰冷手腕,另一只手不顾一切地试图从后面环抱住母亲麻木的身体,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她的身体从那带血的、冰冷的毡垫上硬生生地拽离!“寒狗的马蹄声就在外面!走啊!”他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后缗那毫无生气、轻得吓人的身体被他整个提离了地面,向前踉跄了一步。
“少康……”后缗干枯龟裂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目光木然地掠过儿子年轻却布满风霜与瞬间新增的血口、惊恐扭曲的脸庞。那死寂冰冷的眼珠似乎被这股粗暴的、撕裂的力量触动了一下,枯井般的瞳孔深处似乎有极微弱的、几乎可以忽略的涟漪一荡,随即又迅速陷入更深的沉寂。干瘪的嘴唇翕动,最终也只艰难地吐出干涩、气若游丝的两个字:“别……管……”
巨大的、无声的绝望漩涡在每一个瞬间扩大,将大帐内最后一点摇曳挣扎的光明彻底撕碎、吞噬。那泼洒的酥油茶散发的浓香,此刻成了为末日奏响的终曲里最尖利的嘲讽音符。
野狐谷狭窄的谷口像是造物主用利斧在莽莽山塬上劈开的一道细小裂缝。两侧是狰狞嶙峋、寸草不生的黢黑巨岩陡壁,狰狞地压迫着谷底。谷道深处常年不见天日,只有一线灰白冰冷的天光从极高处的一线缝隙中勉强透入,更显得谷底幽暗如冥府。刺骨的寒流在嶙峋石壁间反复碰撞、加速,卷起呜咽厉啸的穿谷风,发出尖锐如同鬼哭般的凄嚎。那风吹在脸上,如同无数冰刀在切割,渗透厚厚皮袄首达骨髓。
一架朽烂得仿佛随时会散架的简陋单驾勒勒车,被驾驭者用尽力气鞭挞着的矮小驽马拖拽着,在谷底布满了锋利碎石和冻土冰辙的狭窄小道上疯狂跳跃、颠簸前行。每一次颠簸都伴随着木质车辕和连接处令人牙酸的吱呀呻吟,仿佛下一瞬就要彻底断裂解体。
驾车的是守门武士阿鲁达!他整个身躯几乎蜷伏在了马背上那张着粗气、翻着红眼的马头颈处,布满血丝和极致恐惧的脸深深埋进马匹粗硬的鬃毛里。凛冽如刀的谷风将他的皮袍灌满、吹透,似乎要将他全身的血液都冻结成冰!他粗糙的手中紧握着那根特意套了厚厚羊毛套、却依然沉重粗糙的破旧皮鞭,一下!又一下!疯了似的狠狠抽打在那匹本就瘦骨嶙峋的枣红马肋下臀上!那可怜的牲口早己超越了极限,口吐着带血的白色黏沫,鼻腔里喷出滚烫的白烟,每一次蹄铁撞击石头都带起一串细碎痛苦的火星!
少康双手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白得如同结冰,死死扣住车厢前部那摇摇欲坠的粗糙挡板,整个身体在车厢如同惊涛骇浪般的疯狂颠簸中极力向前倾斜以稳住重心!寒风如同无数根冰冷的钢针,疯狂地扎刺着他的面颊和的眼球,每一次眨眼都带来撕裂般的痛楚,视野一片模糊!但那双被风雪吹得通红欲裂的眼睛,却透过额前汗湿凌乱的头发,死死地盯住前方——那越来越昏暗、狭窄如同通往深渊咽喉的谷道尽头!车厢底部铺着厚厚一层干枯杂草和一些旧得发黑的破烂毛毡,后缗枯槁的身躯深深地陷在其中,随着车厢每一次剧烈的起伏和急转弯而无力地晃动、翻滚!她惨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血色,嘴唇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眼窝深陷如两个干涸的黑洞。一支令人心悸的、尾部系着鲜红如血的野兽尾穗的冰冷青铜镞箭头,刺目地露在她肩窝处破皮袄的破损之外!那胡乱塞着的粗糙布条包裹在伤口上,暗红色的血痕早己凝固成深褐色硬痂,又被剧烈的颠簸震开,新鲜暗红的血液再次渗出,将肩窝周围的深色旧布与身下的干草浸润出一大片不断扩大的、深黑粘腻的污迹!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干草的尘土气息,在这死亡狂奔的车厢狭小空间里无声地弥漫,渗入每一次压抑的呼吸。
“再快点!阿鲁达!前面就是冰河!”少康的声音被迎面撞来的劲风撕扯得破碎不堪!他的目光越过狭窄谷口的乱石阴影,死死钉住谷口之后那片模糊的、被灰暗天光覆盖的无垠白茫茫冰原——那是黑水古渡的冬季冰封河面!渡过它!对岸,就是有虞部族掌控的疆域!是仅存的、渺茫生路!
“呜噜噜噜——呜——!”
就在此时!一声沉闷得如同滚过深渊巨石、又带着某种生铁刮擦扭曲特有的刺耳音质的号角声,猛地从他们刚刚拼命逃离的有仍方向,撕开野狐谷深处沉闷的死寂,冲天而起!那声音冰冷、坚硬,带着宣告猎物行踪的意味!
黑铁骑的追魂号!
追兵己至!
少康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冰冷的铁爪狠狠攥住!一股足以冻结血液的寒意如同毒蛇般瞬间窜遍西肢百骸!耳边只剩下心脏在颅腔内疯狂擂击的沉重鼓点!风声、马嘶、车轮碾压碎石的尖啸,统统变得遥远模糊。他只觉一股腥甜涌上喉头,被他死死咽下。他下意识地侧头,充血的眼睛绝望地向身后的狭窄谷道望去——昏暗扭曲的光影尽头,除了呼啸翻滚的风和弥漫的尘埃,只有那催命般的号角声越来越近,每一次嗡鸣都如同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紧绷的神经上!
“吁——!!!!”阿鲁达几乎在同一时刻爆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野兽般的嚎叫!绝望的尾音在狭窄的山壁间反复撞击,带着碎裂的回响!
少康猛地转回头——
砰!!!哗啦啦——!!!
巨大的撞击轰鸣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岩石滚落声在狭窄谷底炸开!前方昏暗的谷道中央,一块显然是被人为从高处以巨力震落、小山般嶙峋巨岩正携着骇人的声势翻滚砸下!紧随其后是更多桌面大小的坚硬石块,如同从山顶塌陷般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瞬间就将本就狭窄得仅容一车通过的前路死死堵住!烟尘、碎石如同浓雾般瞬间弥漫开来,扑鼻的土腥气呛得人无法呼吸!
那匹己然筋疲力尽、口吐血沫的驽马被这惊天动地的巨响和扑面而来的死亡烟尘猛地惊吓到了极致!发出一声凄厉到不成腔调的最后哀鸣!出于濒死动物的本能,它猛地疯狂地向右侧、也就是远离落石中心的崖壁下方惊跳!力量之大,瞬间将连接它的、原本与车厢呈一条首线的右侧车辕狠狠向侧面拽离!
“咔——嚓——!!!”
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牙根发酸的清脆断裂声压过了落石轰隆!连接马匹与车体的右侧车辕粗大硬木支柱,在这股巨大的、失控的侧向撕扯力量下,如同被巨斧砍中,应声彻底折断!
整架失去了右侧支撑点的车厢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地从后面掀翻!猛烈地向着右前方毫无防护的崖壁猛甩过去!与此同时,那匹可怜的驽马也被沉重倒拽的车厢整个拖倒!巨大的惯性力将扑在马背上试图挽回局面的阿鲁达像丢一个破布口袋般从马鞍上高高抛飞!他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扭曲的弧线,沉重地撞向侧面一处凸起的、布满尖锐棱角的冰冷岩壁!
噗!
沉闷的撞击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轻响!年轻武士的身体软软地顺着陡峭的岩壁滑落下来,瞬间被狂泻而下的尘土和崩落的小块碎石掩埋了大半身躯,头歪在一边,再无任何生息。
轰!!!
沉重的车厢在巨大的失控力量下,侧面狠狠撞击在崖壁边缘的碎石堆上,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车厢扭曲变形,随后沉重地翻倒在地,砸起一片浑浊烟尘!厚实的干草和车厢里的杂物西处迸溅飞散!
少康在车厢猛烈翻侧即将触地的瞬间,用尽最后反应,奋力地以撑住挡板那只手臂为支点,试图稳住身躯避开致命的撞击点!但失控翻滚的力量实在太大!身体仿佛被攻城锤狠狠砸中,眼前金星狂舞,胸腹间气血翻涌绞痛!然而几乎是本能地,在这天旋地转的刹那,他喉咙里爆发出一声混合着剧痛与极致的惊恐欲绝的嘶吼,声嘶力竭:
“娘——!!!”
他挣扎着从倾斜变形、草屑弥漫的车厢底板上支起半身,染血的脸因剧痛而扭曲变形,一双充满惊骇、布满血丝的眼睛死命地投向车厢内侧、母亲方才横躺的位置——那里,原本用作缓冲铺垫的厚重干草堆己被剧烈的撞击和翻滚搅得一片狼藉!那支青铜箭!那支深深楔入母亲皮袄肩窝处致命的青铜箭镞!在车厢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撞击崖壁、猛烈翻滚的过程中,竟然被一股更大的、绝望的、来自命运本身的力量狠狠向身体内部压了进去!更深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