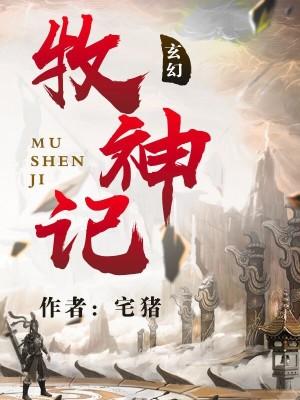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抗日联穿越 > 第56章 帽儿山被服厂(第2页)
第56章 帽儿山被服厂(第2页)
他手臂一挥,指向远方:“我第六军麾下,己有六千余众!控制着汤原、萝北、绥滨大片地区!兵强马壮,百姓归心!这其中,有你文远同志天大的功劳啊!你带来的那些粮食、药品、武器,尤其是那些威力巨大的新式枪械,是雪中送炭,更是如虎添翼!你救了多少战士的命,又让我们多杀了多少鬼子?!”
李文远连忙摆手:“军长,我做的微不足道,真正流血牺牲的是同志们……”
夏云杰打断他,眼神无比真诚:“不,文远同志,你的贡献,独一无二,无人可替代!”
说着,夏军长做出了一个让李文远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缓缓地从腰间解下那把跟随他出生入死、保养得极好的毛瑟C96驳壳枪,连同皮质枪套和几排子弹一起,郑重地双手捧到李文远面前。
“我夏云杰,代表第六军全体将士,感谢你!我身无长物,两袖清风,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这把枪,跟了我多年,算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今天,我把它送给你!见它如见我,第六军上下,永远认你这个人情!”
李文远瞬间愣住了,看着那把手枪,看着夏军长真诚而刚毅的脸庞,只觉得一股热流猛地冲上心头,鼻子发酸,眼眶彻底了。
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把枪,这是一位我党党员、一位抗日英雄能给出的最高级别的感谢和认可!是无价的信任和沉甸甸的情谊!
他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无比郑重地接过了那把沉甸甸的、带着军人体温和战场硝烟气息的匣子枪。
“军长……我……”李文远声音哽咽,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后只化为一句,“为了打鬼子,为了咱们的国家,我李文远,万死不辞!”
在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为了生活奔波、有点小聪明的现代青年,他的灵魂己经深深地与这片黑土地、与这些英勇不屈的人们融合在了一起。
夏云杰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
从根据地回来后,正好遇到外出巡视回来的张政委。
两人也没有避讳李文远,让他一起进入会议室。
按说夏军长和张寿笺政委刚刚经历了一系列战斗和扩张,虽然捷报频传,部队规模扩大,但两人眉宇间却带着一丝忧虑。
在简陋的指挥部里,夏军长指着地图上新扩大的游击区,对张政委和李文远叹道:“老张,文远同志,咱们地盘大了,兵也多了,这是好事。可眼下这心里,反倒更不踏实了。”
张政委接过话茬,语气沉重:“是啊。以前咱们连排级干部,带着十来二十个兵,在山林里跟鬼子周旋,打游击,个个都是好手。可现在,一下子要指挥一个连、甚至一个营,很多新提拔的干部就抓瞎了。怎么组织行军驻扎?怎么协调各部队配合作战?怎么规划后勤补给?这些都不是光凭勇敢就能解决的。”
夏军长点头:“打个比方,一个好猎户,未必能当好将军。咱们缺的是懂正规战术、会带兵、有政治觉悟的骨干军官!战士们光有热情和枪不够,得有人才把他们拧成一股绳,指对方向!”
李文远认真地听着,深刻理解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没有合格的基层指挥员,部队人数再多也是一盘散沙,战斗力会大打折扣。
张政委继续说道:“正好,根据上级的决议,我们要成立一所我们抗联自己的‘黄埔军校’——东北民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军官学校。校长是赵司令,副校长是李副司令,由我担任教育长,负责具体事务。”
他的眼神充满期望,却又带着无奈:“校址我己经选好了,在汤旺河沟里,滚蛋岭东南一个隐蔽的地方。计划每期招收50名各军、师选送的优秀苗子,年纪要轻,身体要好,学习六个月。可是……”
张政委苦笑一声:“我们现在是万事开头难。要啥没啥:没有教材,没有教具,没有地图,没有沙盘,甚至连学员用的纸、笔、墨水都凑不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听到这里,李文远眼睛亮了。这不正是他最擅长解决的“后勤”问题吗?而且这比运送枪支弹药的意义更加深远!这是在为抗联播种未来,培养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