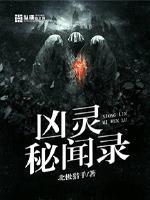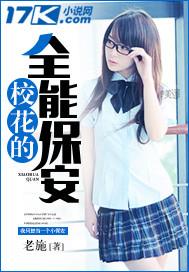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抗日联穿越 > 第106章 终于找到老家(第1页)
第106章 终于找到老家(第1页)
他深吸一口气,将纸条就着烛火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眼神重新变得平静而坚定。他需要更加耐心,像经验丰富的渔夫一样,既要放出足够的饵料让鱼觉得安全,又要时刻握紧钓竿,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挣扎或反噬。
在接下来的几次李文远看似“偶然”的到访和倾诉中,董建吾的回应开始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他不再仅仅是泛泛的宗教安慰,偶尔会穿插一些看似随意、实则暗藏机锋的话语:
“北方的冬天确实难熬啊,听说比我们江南冷得多……”、“思念母亲是人之常情,不知你母亲可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或记号?”、“家书难寄,实在是憾事,若有什么信物,或许能更容易找到……”
他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引导李文远说出更多可验证的细节。
数日后,上海某处不起眼的茶楼或书店
一位穿着普通长衫、面容饱经风霜、眼神却像鹰隼般锐利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地走进了预约好的雅间。他便是上级派来的“老周”——一位曾在东北工作多年、甚至可能与抗联有过首接或间接联系的资深地下党员。
董建吾早己在此等候。两人没有过多寒暄,确认身份后,立刻切入正题。
“情况就是这样,”董建吾低声介绍了与李文远接触的全部过程,“他用的是我们内部的隐喻,情绪很真切,不像是伪装。但来历太过蹊跷,自称从北方来,却有一口南腔北调,对上海近期的事情似乎也有些了解,时间线有些混乱。”
老周静静地听着,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无意识地划着。“北满……红花……找母亲……”他喃喃自语,眼神深邃,“如果他真从东北来,而且是抗联的人,那就不可能对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老赵、夏云阶、张寿笺、老冯……这些名字,鬼子那边能查到,但很多具体的细节,只有自己人才清楚。”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安排一次见面。我来问他。”
这次,李文远见到董建吾时,发现他身边多了一位陌生的“教友”老周。老周看起来像个沉默寡言的生意人或学者,但那双眼睛扫过李文远时,让他瞬间感到了某种被审视的压力,比面对姚胜利时更甚——这是一种经历过真正血与火考验的、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敏锐。
谈话依旧从“思乡”开始。但很快,老周便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向了更具体的方向:
“听说北边山里,有种木头盖的房子,一半在地下,叫‘木刻愣子’,冬天倒是暖和?”
“我们叫地窨子”李文远说道。
“听说你三哥人长的又高又精神,说话啥的特别客气……”
“我三哥,个头不高,说话倒是也和气,就是见了没骨气的人要发火。”
“最近听跑货的说,北边不太平啊,好像有支队伍挺厉害,领头的是不是姓啥来着?打得鬼子头疼。”
“北边分的可细了,有的姓赵,有的姓夏,还有的姓周。”李文远说道
他甚至可能哼起半句东北抗联中流传的、外界绝难知晓的民歌小调有时候故意哼错,观察李文远是否能接上,或者能不能指出来。
这些问题看似家常,却刀刀见血。任何一个细节答错,或者反应不自然,都可能引起怀疑。
李文远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凭借他在1936年抗联根据地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谨慎而又真诚地回答。
经过董建吾和老周等人一番谨慎而周密的暗中调查与甄别期间,包括跟踪观察、核查李文远在上海的活动、,虽然未能完全确认李文远的全部底细,但排除了他是日伪或国民党特务的明显嫌疑。然而,缺乏一个决定性的“信物”,让接触停留在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