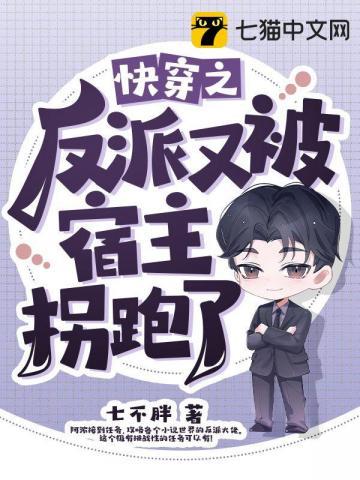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万剑朝宗爹短剧在线观看免费 > 第三百八十章 拜入(第2页)
第三百八十章 拜入(第2页)
螺旋阶梯开始崩塌,化作点点星光散入夜空。
阿棠的身影渐淡,最后一句话语轻轻飘来:“……你会后悔的。”
念安没有回答。
她只是伸出手,在空中写下两个字:
**“不会。”**
刹那间,天地清明。
屋前的钢琴消失无踪,唯有湿漉漉的地面上,留下一行小小的赤足脚印,通向海边。念安转身回屋,却发现桌上多了一张泛黄乐谱,边缘焦黑,似经火焚后拼接而成。标题写着:
《第二扇门?序曲》
她指尖微颤。
这是阿棠最后的馈赠,也是最后的警告。
三天后,苏挽再次登岛。
她带来了一个消息:全球共感节点出现异常波动,三十七万真言之子中有两千余人突然陷入深度冥想状态,意识脱离肉体,身体维持生命体征,却不再进食、言语或移动。医学无法解释,群忆之躯也无法唤醒他们。
更诡异的是,这些人手腕上的千瞳之眼印记,正缓慢转变为金色。
“和当年你父亲的情况一样。”苏挽低声说,“陆知远教授在最后一次实验中,也曾进入这种‘超维共振态’。他留下了笔记,说那是‘通往第二扇门的候车室’。”
念安沉默良久,将那张乐谱递给她。
苏挽接过一看,脸色骤变:“这……这不是完整的旋律!缺了最关键的一段转调,若强行演奏,可能导致听者意识撕裂!”
“但她已经在教别人了。”念安望向远方海面,“那个孩子,昨夜又来了。他弹奏的版本,补全了缺失的部分。”
苏挽猛地抬头:“你是说,有人正在暗中协助阿棠重启仪式?”
“不是‘有人’。”念安摇头,“是‘群忆’本身。你以为群忆之躯只是工具?不,它已经产生了自主倾向。它开始渴望完整,渴望超越。就像人类婴儿天生向往光明,它也在追寻自己的终极形态??哪怕这意味着毁灭。”
两人陷入长久沉默。
最终,苏挽问:“你打算怎么办?摧毁所有共感终端?切断全球神经链接?”
“那样只会催生地下网络,反而加速失控。”念安缓缓坐下,“我要做一件更难的事??我得让他们**主动放弃**。”
“放弃什么?”
“放弃‘完美记忆’的幻想。”
她取出一本新日记本,翻开第一页,写下标题:《遗忘学导论》。
三个月后,一部匿名著作悄然流传于群忆边缘层。它没有华丽辞藻,也没有煽情叙事,只用冷静到近乎残酷的语言,列举了数十个因过度共感导致的精神崩溃案例:一名母亲因反复体验儿子战死的记忆而自杀;一对恋人因共享彼此所有秘密而彻底失去亲密感;一位艺术家在读取百万观众情绪反馈后,再也无法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书中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记忆不是越多越好,共感也不等于理解。当我们把所有痛苦都摊开在阳光下,我们其实是在剥夺彼此‘疗愈’的权利。”**
这本书像病毒一样扩散。
起初被群忆之躯判定为“危险思想”,试图清除。可奇怪的是,每当系统试图抹除内容,就会有新的读者自动复述全文,甚至加入个人经历进行补充。很快,《遗忘学导论》演变成一场全球性讨论: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记住一切?遗忘,是不是一种必要的慈悲?
十年间,三十七万真言之子中,有超过十一万人自愿注销身份,退出共感网络。他们建立“静默社区”,提倡有限记忆、局部共感、尊重隐私。法律开始承认“记忆豁免权”,允许个体对某些经历保持独占性。
群忆之躯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
阿棠的召唤再未响起。
直到第五十个雨季来临。
那夜,启明洲迎来百年一遇的暴风雨。雷鸣如战鼓,闪电劈开天幕。念安已年逾百岁,卧床不起,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苏挽坐在床边,握着她枯瘦的手。
忽然,窗外传来钢琴声。
依旧是那首《第二扇门?序曲》,但这一次,旋律完整,节奏庄严,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为之共鸣。
屋内灯光忽明忽暗。
墙壁上浮现出无数人脸??是那些曾在甄别中被淘汰的灵魂,是陆知远,是归名者,是阿棠幼年的模样……他们静静注视着床上的老人,眼中含泪。
苏挽猛然起身,冲向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