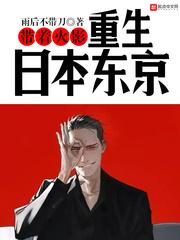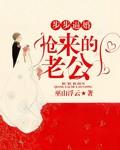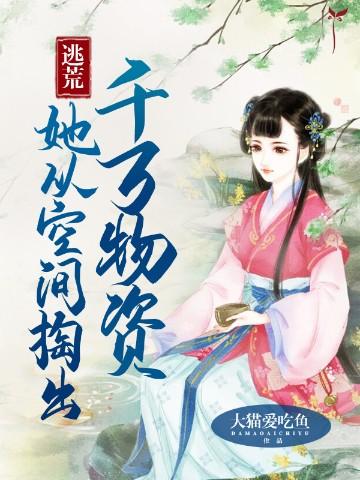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影视都市从四合院开始醉倒不得了 > 第8章 伪装(第1页)
第8章 伪装(第1页)
赵舒城听到左永邦的话,又看到罗书全跟米琪都紧紧盯着自己,赶紧摆手说道:
“那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梦。”
“真的?我不信!”
看到米琪挑衅的眼神,赵舒城说道:“我没必要。。。
夜雨悄至,无声地打湿了四合院的屋檐。肖千喜没有开灯,只坐在办公室的旧藤椅上,听着窗外滴答的雨声,手里攥着那本“未寄之信”的笔记本。她已经很久没翻开它了,可今晚,周子阳那段录音像根细针,刺穿了她多年筑起的平静。
她又翻到了第二页。
>“亲爱的陈老师:
>您说我该叫您‘妈妈’还是‘姑姑’?
>我一直没敢问。
>那年我发高烧,您抱着我在雪夜里走了五公里去医院,手指冻得发紫也不肯松手。
>可第二天,您又把我送回福利院,说‘我不配当母亲’。
>我知道您不是亲生的,
>但您给我的那一夜温暖,
>是我人生里第一次觉得,
>被人当作孩子疼过。”
笔迹在这里顿了一下,墨水洇开,像是泪痕。
>“后来我才知道,您当年也有个女儿,三岁就夭折了。
>您怕再爱一次,心会碎。
>可您知道吗?
>我宁愿做那个让您心碎的人,
>也不想做被推走的孩子。”
肖千喜闭上眼,喉咙发紧。陈老师是她初中时的心理辅导老师,也是第一个发现她自残痕迹的人。那时她刚被亲戚轮流收养,像件没人要的行李。陈老师曾想收养她,却被家人以“血缘之外皆不可靠”为由强行阻拦。十年后,她在一场心理培训会上重逢陈老师,对方已白发苍苍,见到她时颤声说:“我一直留着你的作业本。”
她从未把这封信寄出,也不敢当面说出口。如今,陈老师早已退休,搬去了云南养老。她们最后一次通话,是去年冬天,老人笑着说:“小喜啊,我种了一院子的梅花,等你来看花。”
雨越下越大。手机震动起来,是一条系统自动推送的预警通知:西北某牧区心灵驿站蓝箱内收到一封紧急信件,作者是一名十三岁藏族女孩,用汉语夹杂藏文写道??
>“阿妈喝药死了。她说她活够了,牛羊没了,我也该学会一个人。
>我把药瓶埋了,可我知道我也快撑不住了。
>你们说有人会听,可谁能听懂我说的话?”
附件附有一段语音,只有十二秒。背景风声呼啸,女孩的声音轻得像雪落:
“我想……再见她一面。”
肖千喜立刻拨通当地顾问电话,确认女孩已被纳入观察名单,目前安全,但情绪极度低落。她下令启动“双语共情响应机制”,派遣精通藏汉双语的心理志愿者,并协调当地寺庙的心理援助僧侣共同介入。
“别让她一个人守着坟。”她低声说,“安排人陪她去祭拜,带上经幡和青稞酒。告诉她,哀伤不是软弱,而是爱还在流动。”
挂断电话后,她打开全国蓝箱数据后台,调出近五年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件统计。数据显示,高原与边远牧区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发生率逐年上升,主因并非贫困,而是“语言隔阂导致的情感失联”??他们既无法用母语表达痛苦,又难以用汉语精准传递情绪。
她忽然意识到,萤火计划至今仍以汉语为核心沟通媒介,这对许多孩子而言,本身就是一道无形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