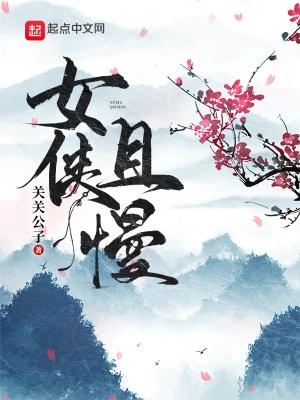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御山河品牌 > 第二十六回 漕浪藏锋联诱才 诗笺传意赴京来(第2页)
第二十六回 漕浪藏锋联诱才 诗笺传意赴京来(第2页)
“未必。”李云舒抬眸,目光与他相接,“碎玉尚可磨,断弦若遇知音,未必不能再续。只是怕那浪头太高,知音难寻,反倒惹一身风波。”
汪康年抚掌轻笑:“公子多虑了。风波之中,恰见真金。若有知音愿为拨弦,纵是惊涛骇浪,亦有逆水行舟之力。”
李云舒指尖一顿,唇角勾起一抹淡笑:“既如此,在下倒愿为先生续一联——‘青衫染恨,官声裂胆毁尽燕尔春’。”
汪康年闻言,眸色骤亮,端起茶盏敬他:“公子才思,果然名不虚传。这‘春’字,藏得比‘喜’字更痛,也更烈。”
“不过是亲历者,更懂霜雪刺骨罢了。”李云舒浅啜一口茶,语气平淡,却字字带锋。
李云舒续完联,汪康年眼底精光一闪,随即敛去,抬手为他添了盏热茶,语气故作热络的生意人模样:“公子才思如神,在下佩服!不知公子贵姓,可否相告?也好日后登门致谢。”
“在下免贵姓李,名云舒。”李云舒放下茶盏,神色淡然。
“云舒?”汪康年眉头微挑,故作疑惑地摩挲着茶盏边缘,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阁下便是李云舒公子?在下初到城阳,尚未站稳脚跟,便已听闻阁下的才名,只道是位白发老者或是饱经风霜的隐士,今日一见,竟这般年轻清朗,实在出人意料!”
李云舒凝视着汪康年,见他虽着粗布长衫,却难掩眉宇间的威严气度,指尖不自觉收紧茶盏,缓声问道:“阁下谈吐不凡,不知是从何处而来?”
汪康年呷了口茶,语气平淡却藏锋芒:“不过是从洛京来的游商,做些漕运相关的买卖,路过城阳罢了。”
“洛京?”李云舒眉峰微蹙,“听闻那里官声鼎盛,漕运更是繁华,阁下既做这生意,想必见多识广。”
“繁华是真,暗流也不少。”汪康年抬眸,目光似不经意扫过他,指尖蘸了点茶水,在桌案上轻划一个“桂”字,随即抹去,“漕浪之下,藏着多少碎玉残珠,外人哪能知晓?倒是城阳,看似平静,却也有浪头拍岸的声响。”
李云舒瞳孔微缩,指尖猛地攥紧茶盏,唇角勾起一抹冷峭:“阁下耳力倒是敏锐。只是这浪头,有时是天灾,有时是人祸,难防得很。”
“天灾易躲,人祸可防。”汪康年放下茶盏,声音压低几分,“若有识浪之人引路,未必不能避开漩涡,甚至……逆浪而行。”
李云舒眼底寒芒一闪,反问:“阁下是说,有人能搅散这浪头?”
“非搅散,是借浪势。”汪康年轻笑,“浪起时,既能碎鸳鸯,亦能载舟船。就看掌舵之人,想往哪处去了。”
李云舒沉默片刻,缓缓道:“掌舵需先辨风向,阁下可知城阳的风,吹向何方?”
“吹向该去的地方。”汪康年语气笃定,“风里藏着冤屈,也藏着希望,就看谁能先握住那风口。”
二人对话间,字字不提正事,却句句暗扣杜之贵的苛政与李云舒的处境,一旁伺候的店小二听得云里雾里,唯有他们二人,目光交汇时,尽是心照不宣的机锋。
李云舒指尖摩挲着微凉的茶盏边缘,目光定定落在汪康年脸上,那双眼眸清亮如洗,却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锐利:“阁下绝非寻常游商。”
汪康年正执壶添茶,闻言动作一顿,抬眸时眼底已漾开一抹玩味的笑意,指尖将茶壶搁在案上,发出轻脆的瓷响:“哦?公子何出此言?”
“游商走南闯北,身上多带市井烟火气,言语间不离银钱货殖。”李云舒声音清润,却字字掷地有声,“可阁下虽着粗布长衫,袖口却无半点风尘磨损,言谈间气度沉稳,眉宇间藏着挥之不去的威严,绝非常年奔波于货栈码头之人。方才论及漕运,阁下只提浪头暗流,未谈半分市价行情,这哪是做买卖的口吻?”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窗外粉壁上的对联,语气添了几分笃定:“更何况,阁下那副对联,字字藏着城阳的隐痛——漕浪拍堤,碎的是鸳鸯喜;官声裂胆,毁的是燕尔春。这些事,若不是亲历者或有心打探之人,绝无可能知晓得这般透彻。阁下初到城阳,便将桩桩件件嵌进联中,若说只是偶然,未免太过巧合。”
汪康年听罢,忽然抚掌大笑,笑声爽朗,震得案上茶盏微微晃动,引来邻桌食客好奇的侧目。他笑罢,端起茶盏一饮而尽,茶沫沾在唇角也不在意,只眯着眼打量李云舒,语气里的玩味更浓:“公子好眼力!不愧是城阳第一才子,仅凭三言两语、一副对联,便能窥得几分端倪。”
他身子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些,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你说我非游商,那依公子之见,我是什么人?是路过的官差?还是寻仇的侠客?”
“我不知道。”李云舒坦然摇头,指尖却不自觉收紧,“但我知道,阁下此来城阳,绝非为了赏景或做买卖。你眼底的锋芒,藏着心事,藏着目的,与那些只为生计奔波的游商,判若云泥。”
“哈哈,有趣,实在有趣!”汪康年又是一阵笑,抬手拍了拍桌案,“公子果然名不虚传,心思缜密,洞察秋毫。至于我是谁——”他故意拖长语调,目光扫过窗外渐浓的暮色,落在远处漕运码头的方向,“眼下还不是说的时候。”
他话锋一转,语气添了几分郑重:“不过公子方才问,对联里的事我是不是初到城阳才知晓——实不相瞒,我来之前,便已听闻城阳漕运苛政,民怨沸腾。只是亲耳听到书生们议论,亲眼见你续联时眼底的痛色,才知这桩桩件件,比传闻中更令人齿冷。”
李云舒沉默片刻,端起茶盏浅啜一口,茶水的温热却暖不透心底的寒凉:“阁下既已知晓,又何必用一副对联搅动城阳?”
“搅动?”汪康年挑眉,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深意,“我不过是抛块石子,想看看这潭水里,究竟藏着多少鱼虾,又有多少人,敢浮出水面罢了。”
邻桌的食客正高声谈论着今日的对联风波,店小二端着热腾腾的包子穿梭其间,蒸汽氤氲了半间客栈,混合着酱肉的香气与茶水的清冽。窗外,暮色渐沉,漕运码头传来几声悠远的号子,与客栈里的喧嚣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鲜活的城阳夜景。而临窗的这张桌前,两人对话间字字机锋,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与试探,与周遭的烟火气格格不入,却又奇异地融为一体。
汪康年指尖摩挲着茶盏边缘,唇角勾起一抹了然的笑,语气轻缓却精准地挑破一层窗纸:“不过在下初到城阳,虽不识公子之面,倒识公子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