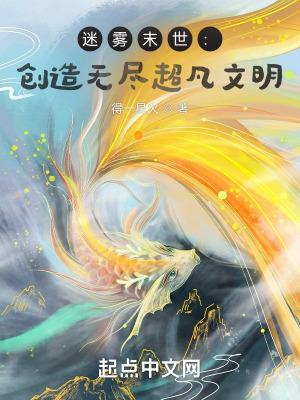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饮鸩止渴! > 二十 不得已(第2页)
二十 不得已(第2页)
直至这一瞬,我才似突然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手舞足蹈地问道:“不对,不对!大舅到来之际变故已然发生,难道他就没将这些人教训一番么?”
“教训了。”阿娘泰然自若地道:“他一气之下将胡老爷子弄成了残废,又把他两个儿子的胳膊给卸了,脸也均给打得毁了容,只是那个老婆子本来就疾病缠身,看着也怪可怜的,就没再对付她了。不过自然,他们管我们要的铜板又都给要回来了。”
我怔怔地听着,刚喝进去的一大口萝卜汤险些喷将出来。
师父又淡淡地接口道:“不仅如此,我还给他们的茶里掺了毒物,主的是精神萎靡,奇痒难耐。他们这叫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买药材、制毒水耗费的时间着实不小,直到胡家子女已经被逼得逃走,我才完成这些。可惜呀,可惜……”
我呆呆地听着,本来还想问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四个恶人的下场,话到此处我心中却已了然了:这四人是生是死,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胡大哥十余年苦心经营的茶馆已经不复存在了。十年来的家业瞬息间沦为泡影,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挽回的了。既然他们已经决心另谋出路,那旁人再怎么干涉想必也是无济于事了。
也不知胡大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有没有找到得心应手的活来做?兄弟四人是否还在一处?他们都是性格极为老实的人,没有被旁人给欺负吧?
正谈话间,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上来一个店家小二伸手要铜钱。我将手伸进怀里,使劲翻腾着,紧接着却是一惊:怪了,我的钱袋子去哪了?
我立时被吓着了,额上不断沁出细小的汗珠,连忙出声询问身边二人。
二人均是一惊,各自慌乱地翻找着。我猛地想起日间的一幕来:在摩肩接踵的点心铺前,似乎曾有好些人拼命般的挤着我,我当时却浑没当回事,一心一意的顾着怎么抢到可人的红豆糕……
我很想说一声:“别翻了,已经被偷去了。”
然而只觉得嗓子干干的,根本说不出话来。腿也已经软了,一颗心在胸膛中高悬起来,耳周烫烫的,浑身像被火炙烤着一般的不自在。然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仍然自顾自地不停翻找着。
小二等得不耐烦了,冷冷地斜睨着我们。
“那个……”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干耗下去了,开口时语气却不太坚定:“要不,我们给您干几天活?”
小二却是浑然不不领情,傲慢道:“我们这里不缺人手了,只缺银子。”
眼见我确实拿不出,他又不爽催促道:“姑娘还是赶紧的吧,我们这客人还多着,可不能总等着你吧?”
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刀俎上的鱼肉,虽然已经万分火急,我还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一瞥眼,之间一位穿金戴银的小姐盈盈进了饭馆,立刻就有旁的伙计上前招呼去了。电光火石之间,有如灵光乍现,我心中妙计横生。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我利索地将头上银簪一举拔了下来,毕恭毕敬递到小二手中。这下我终于挺直了胸脯,朗声问道:“够了么?”
那小二仔细打量着精致的柳银簪,一闪身就不见了。我知道他是拿不定主意,找管事的商量去了。我们三人就这样沉默无言的相对了半晌。
拿掉了银簪,我身上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当初在山野间没心没肺的欢笑之时,哪能料到有朝一日竟会为了生计发愁?一怔间,又有两行清泪唰唰滚落,却不是为了十多年前就与我相识的柳银簪,而是为了我如今苟延残喘的狼狈模样。
我与这银簪也是无缘,其实它早在十年前就该是别人的了。那时的恐慌远比现在要严重,因此也无心替它惋惜。可谁道阴差阳错间,竟是梁浮生将它寻了来,重新交还于我。这样一来,对它的感情竟比十年前更要深厚一些。若非实在束手无策,我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故技重施,将它边卖出去的……也罢,毕竟旧物在侧,难免睹物思人,又徒增伤悲。这银簪一离手,我们之间那点微弱的关联,可就彻底断了……只有一事不妥--这物什,原是阿娘祖传的嫁妆。
我突然握紧了阿娘颤抖的手,这才发现她的眼中似乎也有泪光闪烁。我心头又是一酸,柔声道:“阿娘,女儿没用,弄丢了钱袋,又卖了您给的宝贝……您千万别难过,我以后就陪在您身边,再也不嫁人了!”阿娘一双生满了茧子的手抖得愈发剧烈,她在语无伦次间瞥向了师父。师父的眼中,是一种我看不穿的幽幽的悲伤,阿娘展现出来的却是浓浓的惊恐。
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引得她们为我担心了,却并不想解释,只扯出一个有点苍白的笑来。她们都不知道,我若是再想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或是与另外一个人柔情蜜意的度过余生,此生是不能够的了。
年少自傲不知错,心头抱恨散复生。乞君予情终不果,荒唐此心未安宁。萍水相逢诀别过,遥遥罪孽已难清。
小二很快面带喜色地回来了,还给我们找了一点碎银子。这便足够支撑我们平安走到清欢镇了,只要路上多加小心,别再浑然不觉的遇到贼人。
经此一事,我们三人在路上的话都少了许多,突然生出了一种既沉默又尴尬的微妙氛围,让人好不自在。我想,大概和我那日说自己永不嫁人脱不了干系。不知怎的,对于这件事,师父好像比阿娘意见还大。可她自己也没有成亲,现在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不过我也顾不上这些了,每天只顾着检查这些碎银子还在不在身上,这般小心翼翼的,到好像我才是个贼人。
不负我狠心卖掉银簪的决心,剩下的两日行程中不仅晴空万里,而且也没有再遇到什么歹人了。虽说一切都十分顺利,可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那股空荡荡的感觉,像是失足掉进井里却没摔死的人,余生只能百无聊赖的坐在井底,呆呆地观望着黑黝黝的天空。
可我没在井里,我是在路上了。我回头望了望来的那条路,然而看不见茶馆更看不见胡大哥。我知道,又是一个结束,是高粱镇的十年悄无声息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