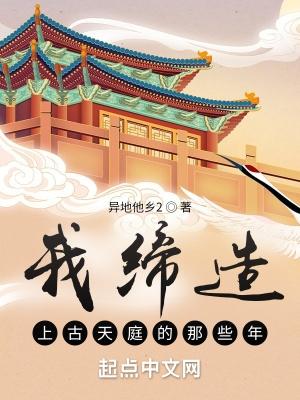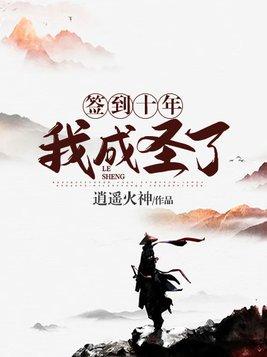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第91章 > 第472章 送命题(第2页)
第472章 送命题(第2页)
祭司久久不语,最终缓缓跪下,将骨杖插入雪中。“若你说的是真……那么,请让我族青年加入修建。我们要亲眼看着桥站起来。”
沈昭扶她起身,郑重拱手:“欢迎你们成为守路人。”
自此,工程力量倍增。达瓦部落派出五十名壮丁,熟悉冰性,擅长雪地作业;更有几位老匠人贡献祖传的“冰榫接合术”,使桥体更加稳固。十日后,十二墩台全部竣工,铁缆成功架设,桥面开始铺设。
就在全线贯通前夕,长安急报再至:永宁侯残党勾结吐蕃边境叛将,意图趁沈昭远离中原之机,策动陇右兵变,并散布谣言称“冰脊道耗空国库,实为私利”。朝中已有大臣奏请罢免沈昭官职,收回金印。
程砚在附信中写道:“局势危如累卵,速归一辩。否则多年心血,恐毁于谗言。”
帐内烛火摇曳,沈昭读完信,沉默良久。
阿箬走进来,见他神色凝重,便问:“要走吗?”
“若我不在,桥还能建成吗?”
“能。”她答得干脆,“但我们都会记得,你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离开的。”
沈昭苦笑:“可若我不回去,一切都会被推翻。这条路,不只是石头和铁,还需要朝廷承认,需要律法保护。”
阿箬坐下,轻轻握住他的手:“那你告诉我,当初为什么出发?是因为圣旨,还是因为那个疏勒老人哭着求你?”
沈昭怔住。
“你说过,真正的奖赏,是有人能安心走过你修的路。”她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现在,这里有更多人在等这条路。你若走了,他们会觉得,原来我们也只是你仕途的一枚棋子。”
沈昭闭上眼,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黄沙下的铜铃、井底的莲花砖、墙上“信者不孤”的刻字、梦中师父的话语……
良久,他提笔写下回信。
致程砚:
“吾志不在庙堂辩白,而在万民足下之路。冰脊道未成,沈昭不归。若有罢黜之诏,愿以庶民之身继续修桥。金印可失,初心不可弃。请代我上奏陛下:路通之日,即是忠显之时。”
信使离去后,沈昭召集全体人员,宣布最后冲刺计划。他将队伍分为三组:一组负责桥面覆冰加固,一组在两岸建造引桥与坡道,第三组则由阿箬带领,设计应急逃生通道??在桥体两侧每隔三十步设置冰洞逃生舱,内置绳梯与暖囊,以防万一。
最后一夜,暴风雪再度来袭。狂风卷着雪片抽打帐篷,几乎掀翻屋顶。所有人都以为必须停工,沈昭却下令全员出动。
“这是最后一战。”他说,“风越大,越要挺直脊梁。今晚不停工,我们就赢了。”
三百余人顶风冒雪奔赴工地。沈昭带头扛起最后一段铁梁,踏着没膝深雪走向湖心。他的靴子早已破损,双脚冻得失去知觉,却一步步走得坚定。阿箬紧随其后,手中提着药箱,随时准备救治伤员。
午夜时分,主桥合龙。
随着最后一颗铆钉敲入,整座桥发出低沉的嗡鸣,仿佛大地苏醒的叹息。那一刻,风突然停了,云层裂开,月光倾泻而下,照在银白的桥面上,宛如银河落凡尘。
老石匠老泪纵横,跪倒在冰桥前:“成了……真的成了……”
达瓦祭司站在岸边,举起骨杖,用古老语言吟唱祷文。牧民们纷纷解下腰带,系在桥头柳树上,那是他们最高的祝福仪式。
七日后,冰脊道正式通行。第一支商队由达瓦部落牵头,载着羊毛、酥油、药材缓缓驶过桥面。孩子们骑在牦牛背上,好奇地俯视脚下幽蓝的湖水,笑声清脆如铃。
典礼上,沈昭并未致辞。他只是牵着那位曾反对他的老祭司,一步步走过桥中央,然后停下,从怀中取出一块小石牌,上面刻着三个名字:央金、扎西、梅朵。
“这是他们的碑。”他说,“立在这里,比埋在风里更有意义。”
祭司颤抖着手接过,泪水滑落脸颊。
数月后,消息传回长安:皇帝览毕沈昭奏章,沉默良久,终下诏曰:“巡道使之职不变,另加‘镇西大夫’衔,赐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于边疆事务。”同时敕令户部拨款百万,设立“丝路复兴基金”,专用于民间修路。
程砚来信笑道:“你赢了。他们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由脚走出来,不能靠嘴争出来。”
沈昭读罢,望向窗外。春意初临,祁连山积雪渐融,溪流潺潺汇入冰湖。桥身稳固,每日过往行人络绎不绝,驿站炊烟袅袅,孩童在柳荫下嬉戏。
阿箬走来,递上一杯热茶。“下一个目标呢?”
沈昭微笑:“南疆有片‘火焰戈壁’,夏日地表可达百℃,商旅难行。我想试试用地下阴渠引雪山水,造一条‘凉道’。”
阿箬点头:“那得找会挖地道的喀什工匠。”
“我已经写了信。”沈昭说着,提起笔,在新地图上圈出一片赤红区域,“而且,这次我想让沿途每个村子都能分到水。”
风再次吹起,穿过桥洞,掠过柳梢,拂动屋檐下悬挂的铜铃。叮咚之声悠远绵长,仿佛回应着多年前玉门关的那一声轻响。
它依旧带着铁镐的余温,掌心的茧,和无数未曾说出的名字。
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