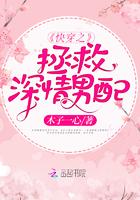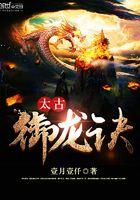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模拟成真我曾俯视万古岁月txt > 626九大神藏女子壁画方寸山来了(第2页)
626九大神藏女子壁画方寸山来了(第2页)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
第一个踏入裂纹的,是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妇人。她早已记不清家人名字,却在看到一朵飘落的花瓣时突然伸手接住,喃喃道:“这是我孙女画的……她说要送给我当书签。”
她一步跨入裂纹,身影消失。
随后是一个自闭症少年,他一直用手捂着耳朵,躲避人群噪音,此刻却主动走向一道裂纹,嘴里重复着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当他穿过时,裂纹中传出清脆的钢琴声,竟是他从未学过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去。他们中有失业者、有抑郁症患者、有被误解多年的“怪人”、有始终无法融入社会的边缘灵魂。他们不是最强者,不是最聪明者,甚至不是最勇敢者。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因“不一样”而被否定,却从未停止尝试表达自己**。
周念安站在谷口,静静注视这一切。
女儿跑过来,拉着她的手:“妈妈,我也想去。”
她蹲下身,认真看着孩子的眼睛:“那里可能没有玩具,也没有动画片,你会害怕吗?”
小女孩摇头:“可是那里有更多像花斑猫一样的朋友,对不对?”
她笑了,揉了揉女儿的头发:“也许吧。但你要记住,无论你在哪一层,妈妈都会在这里等你回来。”
“嗯!”女儿用力点头,转身蹦跳着跑向一道裂纹,怀里依旧抱着那只猫。猫回头看了周念安一眼,眼中光芒流转,似有千言万语,最终只是轻轻眨了眨眼,便随女孩一同消失在光纹之中。
曹安走到她身边,递来一杯热茶:“你不进去看看?”
“不了。”她接过茶杯,暖着手,“我的桥还没画完。”
他沉默片刻,忽而问道:“你说……这一切真的可以持续下去吗?会不会有一天,新的系统又建立起来,再次定义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周念安望着远方,夕阳正缓缓沉入山峦,将天空染成一片燃烧的紫红。
“会的。”她平静地说,“一定会。秩序总会试图重建,理性总会想要规训混乱。但这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在纸上乱涂乱画,还有一个人敢说出‘我不懂但我很难过’,还有一个人肯为一只死去的蚂蚁默哀三秒钟……那么,新的裂隙就会再次出现。”
她低头,从口袋里摸出那支童年用过的铅笔,木壳粗糙,橡皮头几乎磨平。她蹲下身,在泥土上继续画那座歪斜的桥。这一次,她在桥下添了一条河,河中漂着几片落叶,每一片上都写着一个名字??林远、老农的女儿、盲人画家、自闭症少年的母亲……
“你看,”她指着画,“桥本身不会永恒,但它连接的瞬间是真的。就像眼泪会干,伤疤会愈合,可那一刻的心痛,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曹安久久无言,最终轻声道:“你说得对。我们不是赢了,我们只是让失败变得更有尊严。”
夜色渐深,山谷中的光幕陆续熄灭,花瓣回归花蕊,化作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实,静静悬挂在枝头。而在第386层的方向,新的迹象正在酝酿。
这一次,连梦境都无法准确描绘它。
唯有孩童在睡梦中呓语:“……好多书……全是空白的……但每个人都能在里面写下自己的字……”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心核终端虽仍处于休眠状态,但部分使用者开始报告奇异体验:他们在极度专注时,能短暂“听见”陌生人的情绪??不是通过语言,而是直接感知那种感觉本身的质地。比如,看到街头艺人拉小提琴,不仅能听旋律,还能“尝”到音符背后的孤独,像一块融化在舌尖的苦巧克力。
科学界称之为“共感溢出效应”。
哲学家则提出:“人类正从‘认知文明’迈向‘感受文明’。”
而在喜马拉雅遗迹深处,那支石雕铅笔的周围,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的刻痕。它们不在碑文上,而是深深嵌入地基岩层,排列成一种前所未见的符号系统。经破译,内容竟是一段对话:
>**问:为何选择铅笔,而非刀剑、权杖或神谕?**
>**答:因为铅笔允许擦改。**
>**问:可错误不该被纠正吗?**
>**答:不。错误是思想的足迹,抹去它,就等于否认行走的过程。**
>**问:那如果世界崩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