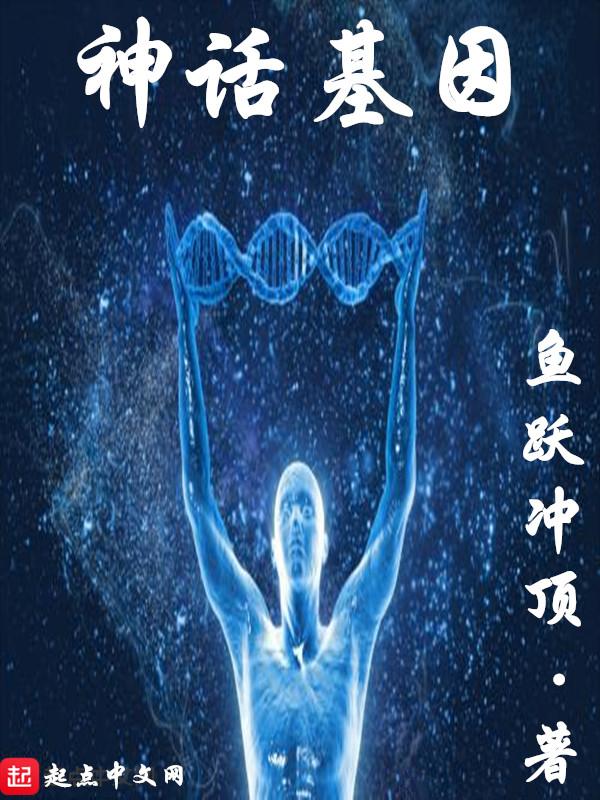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联姻对象他掉马了by全文免费阅读最新 > 4050(第18页)
4050(第18页)
“在吸猫吗饲养员。”顾知宜掌心贴着她脊背,轻轻拍哄,声音低而温沉,像在逗她。
“累。”她的回应很轻。
顾知宜无名指上的戒指透过单薄衣料,压在她脊背上,微凉的金属触感让她想起那枚戒指在他指间勒出的红痕。
她闭了闭眼,“换个戒指吧。”
顾知宜忽然笑了,低头,唇蹭过她发顶,“习惯了。我每次看到它就觉得自己是灰姑娘的恶毒继姐。”
他下一句分外轻巧,“削足适履。”
说完,他手臂一揽,直接托着她的腰和腿弯把她抱了起来。
贝言身体一轻,视线瞬间高了一截,垂眸看他。
“会被狗仔拍到。”她神色平淡。
“那也合法,名正言顺。”顾知宜悠然垂目,浅痣那样生动,抱着她往外走,步伐很稳。
“外套。”他停在衣帽架前,示意她拿。
贝言伸出一只手将他西装勾过来。
顾知宜继续往前走,手臂没晃半点,甚至还能空出一只手按上行电梯。
顾知宜总是可靠过头,贝言干脆搭在他身上不乱动了,扳着他肩膀说,“累。累死了。”
顾知宜低笑,呼吸扫过她耳尖:“不准死。”
她就问:“假如。假如我真的死掉。”
“那也跟你一起。”顾知宜答得太快太镇定,像早想过千万遍,“那里太苦了。”
贝言一听侧头问:“因为我去的地方太苦了所以要陪我去啊?”
顾知宜摇头,把她往上托了托,脸颊贴着她被夜风吹凉的耳朵:
“被你留下的话太苦了。”
贝言的喉咙彻底哽住。
她想起葬礼,想起雨滴与泪滴,想起某个人抱着小纯说让她回来…
…顾知宜忽然感觉脖颈被圈紧,他侧目,腾出手哄着她拍一拍。
“睡吧,抱你回家。”
“行。”
贝言其实睁着眼睛。
…
三天后,她去洺港行程出差时见了温复,让温复替她调查一件事。
温复办事效率很快,再加上这件事确实太紧要了,于是在第五天,贝言就得到了想知道的信息。
回去的时候,温复目光复杂地看着她,那是很少有的事。至少在他这么个吊儿郎当的人身上很少看到。
可贝言摇头笑了笑,示意自己没问题。
她一旦决定要直面什么事,行动力就很强,连夜坐飞机回朝港。
候机前,她拨通了一个电话。
铃响四声,电话那头传来慵懒嗓音,“嗯饲养员有别的猫了?出差一趟不要我了?”
贝言握着手机,也许是因为听到了对方的声音语气平静了不少,“在哪里顾组长。”
“游轮上。”顾知宜声音懒散,背景隐约有海浪和钢琴声,“盛家的订婚宴,都在呢。还问起你来,我说出差。
“我喜欢他们来问我这些,也喜欢替你回答这些。”
顿了顿,他又笑:“想我了对不对。”
光听见这声音,就能想象到他也许眯着眼睛,总是从容。
贝言还没接话,电话那头,顾知宜的声音忽然低了几分,像贴着话筒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