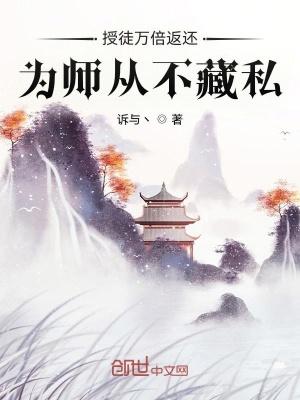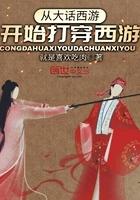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死对头竟觊觎我 > 狼星起(第3页)
狼星起(第3页)
昔日的李昭,是长安城最耀眼的骄阳,纵马横枪,意气风发,如出鞘之利剑,一双桃花眼总是带着明亮的笑意。而眼前的徐福,却像一株生于阴暗角落的幽兰,昳丽,脆弱,带着一种令人心惊的破碎感。常年的苦难磨去了他所有的阳刚之气,只余下这般雌雄莫辨的绝色容颜,连那双眼睛,也只剩下冰冷的死寂。
加之军中那些不堪入耳的流言,崔明度无论如何也不敢将这个委身于人的“禁脔”,与那个骄傲到骨子里的故友联系在一起。
“长安已失,叛军锋芒正盛,此时太子诏我等入灵武,怕是想借朔方军之势,稳固他新帝之位。”崔明度压下心中杂念,将文书递给陆重山,“这是我刚收到的消息,郭子仪将军已兵出井陉,欲东出河北,牵制叛军主力。我等若西入灵武,时机正好。”
陆重山接过文书,一目十行地看完,点了点头。他的目光转向李昭,问道:“徐福,你怎么看?”
这一问,让崔明度再次愣住。
他没想到,在这种军国大事上,陆重山竟然会开口询问一个“男宠”的意见。
李昭抬起头,迎上陆重山的目光。他知道,这是陆重山又一次将他推到台前。他不在意旁人如何看他,他要的,只是一个能让他施展智谋、撬动棋局的机会。
他的目光在舆图上缓缓移动,从朔方,到灵武,再到长安,最后落在了更东边的范阳——安禄山的老巢。
“去灵武,是必由之路。”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病弱的沙哑,但在安静的帅帐中,却异常清晰,“但不能只去灵武。”
崔明度眉头一皱,正要开口,却被陆重山一个眼神制止了。
李昭伸出苍白修长的指尖,在舆图上轻轻划过一道弧线。“太子新立,根基不稳,急需外力支持。朔方军是他最能倚仗的力量,此时前去,是雪中送炭。我等不仅能得到补给,更能借新帝之名,名正言顺地统领各路勤王兵马。”
“但,”他话锋一转,指尖点在了长安与洛阳之间,“我军不能全数西进。收复两京,才是平叛根本。若全军入灵武,便等于将主动权交到了朝堂那些文官手里。届时,我等便成了新帝手中的一把刀,指向哪里,全由不得自己。”
他的声音不大,条理却清晰得可怕,每一个字都敲在了关键之处。
“依你之见,该当如何?”陆重山追问道,眼中流露出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欣赏。
“分兵。”李昭吐出两个字,“将军亲率主力入灵武,面见新帝,稳定人心。同时,留一支精兵于此,做出整军备战、随时东进的姿态,对关中叛军形成威慑。”
他顿了顿,继续道:“如此一来,对内,可让新帝安心,表明我军并无拥兵自重之心;对外,可令叛军不敢轻举妄动,为郭将军在河北争取时间。更重要的是,”他抬起眼,眸中闪过一道幽光,“将军手握勤王主力,人在朝堂,心在战场,进退自如,方能成为执棋之人,而非他人棋子。”
一番话说完,帐内一片寂静。
崔明度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病弱的青年,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这番见解,老辣深远,这份洞悉全局的战略眼光,除了那个人,他再想不到第二人。
这份智谋,这份风骨,即便蒙尘,也依然是他。
“你……”崔明度喉结滚动,声音干涩,他死死地盯着李昭,像是要从那张过分美丽的脸上看出什么破绽。“你是……李昭,对不对?”
李昭闻言,连眼睫都未曾颤动一下。他缓缓抬眸,看向崔明度,那双桃花眼里没有故友重逢的惊愕,只有一片漠然的空洞。“崔先生,认错人了。”
陆重山不动声色地向前半步,恰好挡在了李昭和崔明度之间,语气平淡道:“明度,你累了。”
崔明度看着陆重山维护的姿态,再看看李昭那双再无半分昔日神采的眼睛,心中最后一点希冀也化为冰冷的碎片。他明白了,李昭不想认,或者说,不能认。他狼狈地移开视线,朝着陆重山拱了拱手,声音沙哑:“是……是我唐突了。”
他说完,再也不看李昭一眼,仓皇地转身掀帘而出。无人看见,他藏在袖中的手,正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帐内重归寂静,陆重山看着崔明度离去的方向,眼眸深沉。
“好。”他转过身,对李昭沉声道,“就依你所言。”
他转身,对着帐外传令:“命王大石传我将令,三军即刻拔营,开赴灵武!”
随着将令传下,沉寂的朔方大营瞬间活了过来,人声马嘶,铁甲碰撞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崭新的、更加混乱的棋局,就此拉开序幕。
李昭依旧站在舆图前,看着那个代表长安的标记。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肩上柔软的狐裘,心中一片冰冷。
他的复仇之路,即将正式开始。
而陆重山站在他身后,高大的身影将他完全笼罩。他看着李昭清瘦的背影,看着他眼中不加掩饰的恨意,心中没有半分不悦,反而升起一股安定的感觉。
恨吧。
只要这恨意能支撑着你活下去,只要你能站在我的身边,哪怕你手中的刀随时会刺向我,我也甘之如饴。
他伸出手,轻轻覆盖在李昭冰冷的手背上,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温暖着他。
“路还长。”陆重山低声道。
这一次,李昭没有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