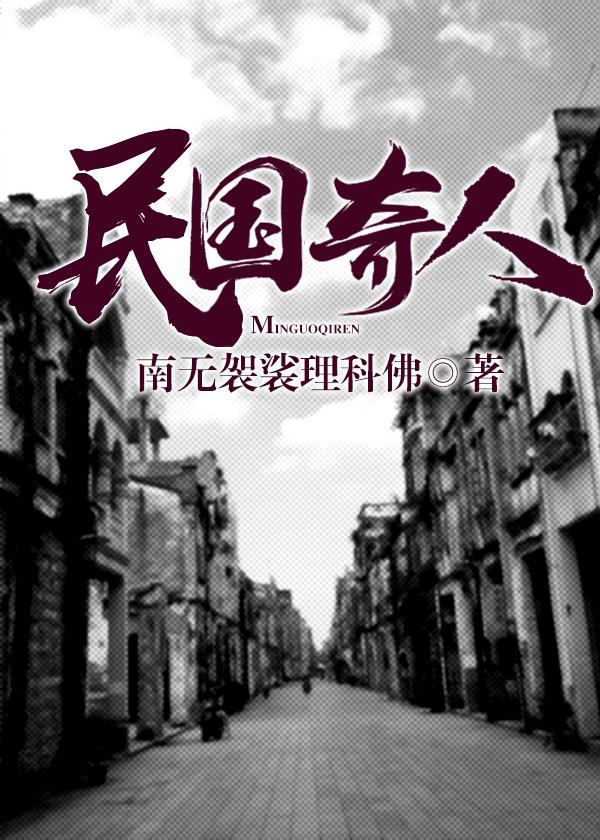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剑网三霸伞联姻视频 > 麒麟折仙(第4页)
麒麟折仙(第4页)
杨姮好笑地戳了戳她的脑袋,书音连忙捂住额头,苦着脸嚷嚷:”小姐都要迟到了,还有心情跟我闹!“
杨姮确实迟到了,匆匆赶到书院的兴文斋,叔父和卫先生在亭子里围炉煮茶,茶水已经滚了三遍。
两个老朋友阔别数年,重逢时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杨姮不欲打扰,悄悄跪坐在一旁,半个时辰后才被里面的人发现。
老家伙直呼大意,慈爱地把这个最看重的后辈拉起来,问她几时到的?吃了饭没有?怎么跪在外面不出声,风吹跑了如何是好?
杨姮莞尔,卫先生是她的授业恩师,六年前应诏去翰林院供职,如今告老还乡,年近六十的人了,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
她一一回答,至于最后那个问题,她故意阴阳怪气道:“当年被您逼着背了那么多书,肚子里的墨水千斤重,大风刮不走。”
“哦?”两个老家伙惊奇地对视一眼,随即哈哈大笑,卫先生捧腹道:“都说女大十八变,这丫头倒还是跟她小时候一个样,看起来是个乖娃娃,一张嘴就知道厉害!”
叔父笑道:”她管教学生的时候更厉害,你住几天就知道了。“
卫先生恍然大悟:“哦!我听说增设琴课是你的主意,那么逼这些娃娃弹《胡笳》的人也是你咯!”
杨姮不爱听这话:“什么叫逼他们学?这曲子又不难。”
卫先生捋着胡须:“《诗经》也不难,当年你不也背得哇哇哭?”
杨姮恼了:“先生欺负人,怎么老拿我小时候说事!”
卫先生哈哈大笑,像从前那样爱怜地摸了摸她的脑袋:“人老了,就喜欢念旧,尤其你这种我看着长大的孩子,知根知底,看见就欢喜。《胡笳》写的是征人怨,那些半大的孩子连太原城都没出过,又怎么会见过守边之人的眼泪?他们弹出来的怨,哈哈,恐怕都是对你这个夫子的怨哟!”
杨姮低头凝思,俯身拜道:“弟子受教。”
卫先生把她扶起来:“好了,不说这个,我上回托人送来的琴,你可弹了,还喜欢吗?”
“喜欢,”提到那张琴,杨姮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眉梢眼角都染上惊喜的笑意:“那张琴真是好极了,我用它弹《阳关三叠》,真真是一唱三叹,连琴弦都在悲鸣!”
“我正想问您,这琴出自谁手?自古琴师斫琴都要留下记号,怎么这张琴什么都没有?”
卫先生和叔父对望一眼,似乎都在询问对方:你没告诉她?
不过眼神只交汇一瞬,两个老朋友就默契地达成了共识,卫先生摸着胡子,一副高深莫测的语气:“一个不愿意留下姓名的人,他说自己一生只斫一张琴,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何必让人知道他是谁呢,更何况,若是得到琴的人觉得这琴不好,知道了他是谁,岂不是要指名道姓地骂他?”
杨姮知道卫先生在胡说,不过她也乐得配合,双手合十望向窗外:“好吧,那就请风儿告诉他,我喜欢这张琴,绝不会骂他。”
三人笑闹了一阵,卫先生忽然撑着站起来,“好了,我今天还约了一个学生,该走了。”
他起身不稳,杨姮连忙扶住胳膊,关切道:“您行动不便,何不叫他来书院相见?”
卫先生“唔”了一声,拄着拐杖望天说道:“有些事,强求不得,双方都愿意才行啊。”
杨姮听不懂,心想这又是什么谜语?不猜了,她才不搭腔呢!
三人路过问心斋,恰好一群孩子下课了蹦蹦跳跳经过,卫先生指着其中一个对老朋友说:“嚯,你瞧那小子,胳膊跟藕节似的,长得多结实!”
驻足看了一会儿,又说:“我那个学生小时候也长得跟他一样,小牛犊似的,天不服地不管,他爹妈可头疼了,但这孩子长得好,家里给起了个小名叫麒麟,我就特别喜欢叫他麒麟小子。”
杨姮起兴致了,新奇道:“这个小名倒有趣,我倒想看看长得有多好,配得上这两个字。”
卫先生看了她一眼:“你又不是没见过。”
杨姮先是惊讶,突然想到刚才跑过去的那个孩子,摇头道:“我没看清,他跑得太快啦。”
卫先生失望摇头,对老朋友欲言又止,表情仿佛在说:“你看这个傻丫头!”
杨姮看不懂他们眼色,只感觉自己平白无故遭了一顿嫌弃,刚想叫屈,卫先生又继续讲起了故事:“不过麒麟毕竟是瑞兽名,后来他爹妈怕这个小名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万一别人以为他们这里真出了个瑞兽怎么办?传到圣人那里,说什么河朔天降祥瑞,那他们儿子就要被献到宫里去了!”
卫先生说得有鼻子有眼,杨姮更觉得好玩了,笑道:“真是异想天开,哪会有这种事,我小名叫月娥,我爹妈怎么不担心我会飞到天上去?”
正说着,三人走出了问心斋,马上就到书院门口了,杨姮银铃般的笑声戛然而止,愣在了原地。
一个许久不见的故人,牵着马车的缰绳侧身而立,在他听见杨姮的笑声转过头来时,杨姮也正好看清了他,四目相对,刹那间万籁俱静。
柳须阳瘦了好多,杨姮记得第一次在醉仙楼见到他时,这男人一身绛紫色花边圆领袍,懒洋洋站在那里,踩着长靴的脚岔开一只,膝盖顶出来,微微露出一截白色的裤腿,她当时就觉得,这人长得真好,矜贵又散漫,像皇宫里出来的侍卫。
可短短半年,他的意气竟消磨成了这个样子。
脸瘦了,也黑了,像被什么人抓到深山老林的庙里磋磨许久,当了苦行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