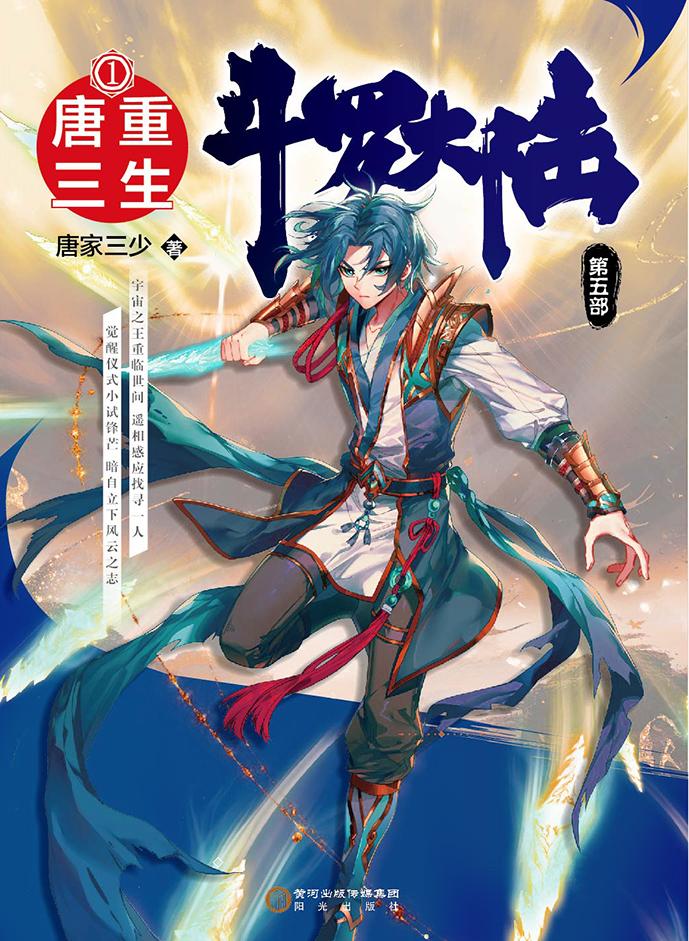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你不是我的白月光下一句 > 7第七章(第2页)
7第七章(第2页)
眼眸稍稍一抬的瞬间,不由发觉,有一双眼睛也正紧紧地盯着她。
那目光落在身上,好像漫天的雪都在往林鸢一个人的脖子里钻。
“你是——”她抬起了头,张了张口,无声地说了两个字。
那日,他在梅林里说:“你会知道的。”
现在,她知道了。
周身更冷了。
连血也冻上了。
“自请受罚?不知道的,以为是要拦着路告御状申冤呢。”萧珣声音淡淡,那目光只停留了瞬息,就随着脚步向前迈,移了开去,撂下了一句,“雪太大,别让人跪外边了。”
林鸢提起裙子,在长御阴沉的眼色中,往廊庑下跪去。
倒是皇帝身后的华服女子,样貌温婉,面色柔和,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许久,最后温言细语地让她免了跪。
那也是林鸢第一次见着瞿皇后。
想到这儿,她“嘶”地吸了一口气。
“烫吗?”林榆伸手往杯腹探了探温。
林鸢把脸埋在耳杯里,摇了摇头。
“那就快些喝了,乖啊。”林榆拍了拍她的头。
林鸢红了脸,刚想说,别再把自己当小孩了,却见林榆回了身,对着一盏翠屏,道,“老四,还发着烫呢。什么时候能退烧啊?都一夜了。”
一夜了?
林鸢愕然,朝外看去,透过窗纱,见天色苍茫,不知隅中,还是日昳,而床榻边上置着一个铜盆,水上浮着白,是未化的雪。盆上搭着两块拧干了的方巾,方觉自己额上有些湿漉漉的。
屏外传来了贺季的声音:“林兄,我的医术,你还信不过吗?小小风寒而已。莫急莫急。”
林鸢恍然,季是行四,所以贺季又被叫做了贺老四。
真是促狭人。她不禁笑了。
林榆见她笑,放下了心,往她嘴里塞了一粒糖渍青梅,笑问:“你说,你百里兼程地赶过来,就是倒也要倒在我这儿,是知道这书院里头有个神医?”
林鸢抿唇,蜜饯在嘴里爆开了甜味:“我还知道,淮阳的蜜饯,比长安的好吃呢。”
林榆也朗声笑了起来。
“哎,不过,芝麻饼定然不及长安的好。”林鸢忽然想起来,指了指自己一路上越发扁了的包袱,“那里头有阿母做的芝麻饼。我大老远带来的。”
“芝麻饼”三个字让林榆惊喜不已。
林鸢看他眉飞色舞,一边取过包袱,一边对贺老四讲着自己阿母的厨艺,如何惊天地泣鬼神,勾得那贺季还没得及问出一句“那为何你们二人,都养得这么瘦呢?”就开始摩拳擦掌,急不可耐地往那包裹里一道翻瞅了。
林鸢心里只能暗怨:“怎么比见着我还高兴?”
她往枕上一倚,又叹出一口气。
她的兄长从模样,到性子,到气质,与铁匠出身的阿父,庖人出身的阿母一点都不像,除了林榆身材颀长,轩然霞举以外,他能骑马挽弓,知诗书六艺,好像生来就会了,至少,从林鸢认得他的时候,就会了。
可眼前的乐陶陶,不正与阿父如出一辙吗?
这样看去,林榆与萧珣,就更不像了,尤其是那份眉眼。
两个冻得梆梆硬的芝麻饼,从包袱里被翻了出来。
“咚”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