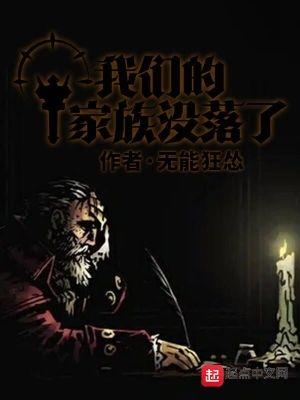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魔尊总想父凭子贵 > 绿蚁第二8(第3页)
绿蚁第二8(第3页)
三年前,他和裴见濯并不是很亲密的关系,李知微热脸贴了一年的冷屁股,才换得他偶尔应几句声,愿意掀起眼皮看他两眼。
背篓太沉太旧,走到门口散了架,呼啦啦大厦将倾,李知微蹲在地上一样样捡,见濯走到他跟前,帮知微抱了几本书回家,看见善思在院子里踩影子,又看见落锁的两扇房门。
“撒谎。”李知微说。
“不信算了。”裴见濯说。
李知微也很想相信,相信裴见濯是随口要的房间,而不是为了帮助一个生计艰难的同学,帮他多要一些地方,哪怕这个同学后来和他发展了亲密关系也一样。
当时他帮我,什么也不图,连□□也不欲求。
可我图他!
我保证,李知微在心里唤起阿閦佛,祷告道,我发誓。
如果未来有那么一天。
他仰起头,望着裴见濯,誓言就此停止。
他该怎么许诺,许诺给他一切的荣华富贵,还是许诺他永生永世不离不弃?前者见濯视如烟云;后者,听起来像他反赖上去那样。
万一见濯不喜欢他了,不离不弃也是一种累赘。
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都是永远啊。
多吓人!他那时候稍稍有些理解了韦弘贞,大概人在不过脑子的时候都爱说这种话,他想来想去,不断措辞,最后说:“见濯。”
“嗯?”
“你樱桃汁染到牙上了。”
人在一起久了,美丑香臭都无所遁形。裴见濯低头,用牙蹭李知微的唇,李知微望着他,望着他,誓言就阻塞住。
李知微相信誓言的力量,所以,每次发誓都慎之又慎,说不出惊天动地的话语。
因为他只能管好自己,管不了别人,譬如他爱善思而不要求善思爱他,也很能理解自己的泰山与岳母。
怎么发这个誓呢,用喜欢或者爱也不行,不要说两个男人,就是夫妻之间,十几二十年后也不谈这个了。
想来想去,再三修饰,他对自己说。
“李知微,从今以后,无论如何,他要你一天,你在一天,这样就得了!”
裴见濯没听见,也不用知道,誓言只对发起方有效,他又不要求共盟。
只是眼底滚下一颗泪来。
裴见濯笑了,指腹拂过那滴泪痕:“心疼我?”
李知微声音微哑:“嗯。是我连累了你。”
裴见濯说:“你心疼就行。”他有些站立不能,扶着桌沿坐下,拍拍李知微的手:“你只用心疼,不要觉得连累。这事对我来说就是挨一顿打,在你身上不一样。”
李知微知道。
皇帝何等铁血,与其说是伤心稚子,不如说是恨自己绝后。裴见濯酿酒,还可以说是贪玩不羁。
李知微酿酒,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善思再无前程,他本人轻则退学,重则除籍,像条落水狗带着幼子无声无息死在永乐城某个角落,亦或是此生此世,仰赖裴见濯的怜悯过活。
裴见濯出来顶罪是对他的最优解,却不是对自己的。
李知微带着满腹算计过来,却原地生出无措,他太久太久没有享受过别人无私赠与了,见濯的爱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