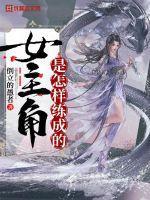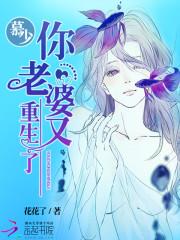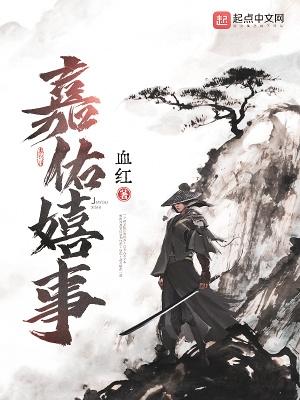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80年代动画片神笔马良 > 170180(第32页)
170180(第32页)
再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联系华夏外贸部——其他出版社一直都如此联系。
闻慈听着这些周折,自己都觉得很麻烦了,但还好社长没有觉得这非常麻烦。
他仍然坚持,最后百转千回地找到了闻慈,于是就有了两人的这通电话。
社长给出了一个符合市场的版权引进价格,闻慈也就答应了,由于两国的距离较近,中间的联系也比和其他出版社沟通要方便——起码他们没有跨越几个时区的白天夜晚。
手握自己响当当的成绩,闻慈再次开始思索,将《小龙历险记》在国内出版的事情。
现在已经快到十二月了,她这几个月十分忙,自打被之前那个出版社气过一通后,就把这事抛在了脑后。除了学校的事情,还有全国美展的事情,提名评比已经结束了,她的《午门》进入了最终提名,但具体能不能得奖,还要等明年展览的终评。
因为这事,闻慈最近莫名其妙收到很多信件。
国内其他美术学院的学生、非学院的在野画家,甚至同学校的一些学生,也给她写了信,她这个名字目前在美术界是稍有点名气的,不用费劲打听,就知道她在哪里。
首都美术学院?嗯,她就在那儿上学,那就往那儿寄吧。
除了褒赞她有开创之风、现实主义的一部分信,也有不少骂声,时代的变革总是两股甚至多股力量纠缠抗争的,闻慈这个紧跟着螺旋跑到前头的人,自然也承担了许多非议。
她倒不在乎那些骂声,有美术报来采访时,她还开玩笑说:“写信给我费了不少邮费墨水吧,大家的鼓励我收到了,反对也收到了,我会朝着我理想的路头也不回地去的。”
他人的反对,不会成为她前进路上的哪怕一颗小石子儿。
闻慈把国内有可能答应的出版社再三考虑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在首都找。
因为她实在没有时间跑其他省市,而如果不盯着印刷美术的话,她又实在放不下心。国内毕竟没有出绘本的先例,她怕没有自己盯着的话,最终会变成不伦不类。
那别说给孩子们看了,她都觉得可能变成自己的黑历史。
闻慈再三挑选,最后选择了一家首都城西的少年出版社。
现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儿童出版社,因为专门为儿童创作这个概念是近些年来才有的,在更早以前,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所有人都经受和成年一样的教育,看《大学》《中庸》,学《论语》。
作家主要为成人写作,而少有为真正的孩子写作,他们的这方面需求是被漠视的。
闻慈私以为,这也是国内绘本行业在几十年后仍没有发展起来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所有家长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孩子、教育孩子,但实际上并不怎么真正重视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发展,让他们受教育是为了往后在社会立足,从拥有好的成绩到拥有好的工作。
至于其他的呢?那不重要。
闻慈找到的这家出版社,眼下就面临着这种窘境。
他们出版社的年纪非常轻,历史还不到十年,在过去那些年里出版了非常多的连环画、一些音乐体育方面的科普书,本来就发展平平,全靠国家支援,国营企业没有倒闭。
但现在改革开放了,尤其是近几个月,所有人都在书店抢着购买外国小说,他们看《基督山伯爵》《红与黑》,连孩子们也有《鲁滨逊冒险记》之类的,他们最近几个月出版的书没有一本不亏本。再这样下去,他们可能要不了*两年就倒闭了。
没听说吗?上个月郊外就有家小工厂被关了,员工都合并去了其他单位。
闻慈拿着绘本找上门来的时候,社长是不可思议的。
“你说,你想在我们出版社出、出这个——”社长一时间忘记了闻慈刚才说的用词,他端起茶杯喝了口,神色有些尴尬。
闻慈镇定地介绍:“绘本。”
“对对,绘本。这是什么东西?”社长又放下了茶杯,不解地问。
闻慈想了想,客观地说:“这个东西主要是从西方起源的,但是“绘本”这个用词是来源于日文,和我们的小人书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大相径庭。它以插画为主、兼顾少量解释的文字,我画的这本是儿童绘本,面向的主要是三到八岁的儿童。”
社长一下子就听懂了,“这是国外的?”
“形式是来源于国外的,但这是我自己画的,”闻慈把绘本推过去,“您看看?”
社长把放在桌上的眼镜擦了擦,架在鼻梁上,很认真地端详起面前几本“绘本”,中间那本他是认识的,硕大的华夏字儿,“小龙历险记——”
他念出这几个字,又疑惑地问:“旁边这几本是什么?它还分系列?”
“不是的,”闻慈忙解释起来,她指尖点了点最左边那本,“这是它在大不列颠出版的版本,”点点最右边那本,“这是今年在意国出版的意语版本。”
最后,她绕回中间,“这是在港城出版的繁体字版本。”
社长惊异地看着面前几本红色封皮的书,声音都尖了,“都出到国外了?”
“这是完全合规,经过外贸部中转出版的,都是大出版社,您放心,”闻慈力求证实自己这是正经事业,不是路边偷印的,她又补充说:“前几天还有岛国的一家出版社联系我,想出它的日语版本,目前还在商定合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明年年初它还会在岛国出版。”
社长一下子重视起来了。
哦呦,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书啊?这是能远销好几个国外的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