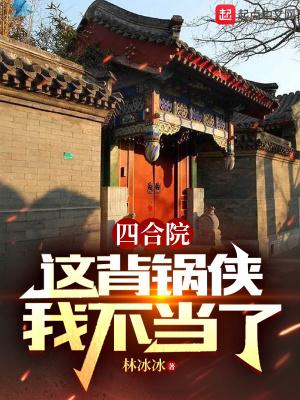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回航天气晴 风信舟 免费阅读 > 6070(第18页)
6070(第18页)
手机依旧没什么信号,登车前骆望钧给她拨过一通电话,她当时忙着检票没有接,现在想起来心里就有了一个疙瘩。他还什么都不知道,童弋祯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那个在感情中踩跷跷板的人。
她走之前给了骆望钧希望,现在又在旧情人面前心神摇曳。
徐稚闻以为她走神是因为饿了,端着在车上买的两桶方便面去泡。
没过一会,童弋祯就听到外面传来争吵声。
“你没长眼睛还是没长耳朵!都和你说了借过,还能撞上,这可不关我事。”
一脸横肉的男人被旁边的热心乘客扯住:
“恁咋不讲理,明明是你撞了人家,开水都烫…”
两个人吵得起劲,徐稚闻却只是安静站在一边,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怎么了?”
童弋祯看到他的手被开水烫得很红,举在半空微微发抖。
徐稚闻眼神闪躲,他听不到童弋祯说什么,只垂着头沉默。
“你撞了人,道歉。”
童弋祯侧过身,挡在他身前,冷冷的声音对上面前嚣张的男人。
乘务员听到这边的动静也走过来,那男人见势不妙,低声暗骂了句什么就逃之夭夭。
童弋祯很无奈,整个过程徐稚闻都安静地站在她身后,甚至另一只手还端着没来得及冲水的泡面。
她从乘务员那里要了烫伤膏。
“别动!”
徐稚闻刚刚经历了短暂的失聪和耳鸣,他知道这是正常的恢复反应,可还是会感到恐惧。
童弋祯扯过他的手,凉凉的药膏挤在手背红肿的地方,瞬间缓解许多。
“我没事。”徐稚闻说。
童弋祯没看他:“你刚刚怎么不骂回去,没长嘴。”
她觉得现在的徐稚闻确实有点奇怪,他从前最是桀骜的一个人,虽然嘴上不说什么难听的话,可待人还是有棱有角,语气里会藏着锋芒,遇到让自己不爽的事当下就会驳回去,还让人挑不出错。
可自从广州见他,就觉得他像变了个人,有种平静却绝望的感觉。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童弋祯说。
徐稚闻看着她忽然就不知该怎么开口,他难道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告诉她,自己患过肿瘤,即便做过手术,也还是聋了一只耳朵吗。
“算了,你当我没问。”
童弋祯理解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那些或许是不堪回首的过去,或许是不合礼教的叛逆,有秘密并不是罪,如果他不愿意分享,自己也没资格追着讨着去问。
她将泡面推到徐稚闻面前:
“吃吧,一会熄灯了。”
童弋祯拿着药膏去乘务室归还。路过车厢连接处,看见先前撞到徐稚闻的男人在抽烟,脚边放着一个软塌的皮包。
她在男人探究的眼神里停下来,对着皮包就是一脚。
那人刚要发作,就听到不带任何情感的直白威胁从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嘴里吐出来:
“你买的是硬座吧。”
男人刚挥起的手垂下来,他确实图便宜买了硬座,又嫌座位太挤不舒服,找了机会一节一节车厢窜过来的,如果要乘务员知道肯定会把他赶回去。
那可就太丢人了。
“而且这里也不让吸烟。”
童弋祯仰头睨着男人,在对方青一阵白一阵脸色里,抬腿又是一脚。
既然有些人不会道歉,那她也没必要端着素质。
等她回到铺位,徐稚闻已经吃完收拾好躺在上铺了。童弋祯抬头看了一眼,瞥见他翻身留给自己一个圆溜溜的呲着头发的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