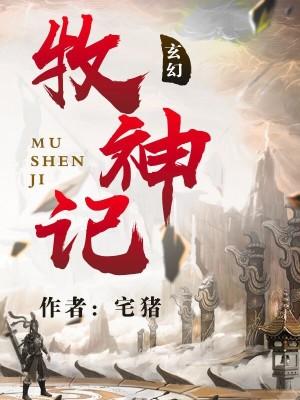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女王受 > 第262章 胜利的剧本(第2页)
第262章 胜利的剧本(第2页)
这句话听上去像在吹捧,但我清楚,他是在阐述他的“剧场国家”理论。
他把我变成了舞台的焦点,不只是权力的中心,更是希望的容器、胜利的预言者、悲悯的象征。
所以我必须一首出现。
我必须站在燃烧的废墟前,说“牺牲不会被遗忘”;
我必须走入新建的学校,说“我们会给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
我必须在墓碑前低头,在圣堂前祈祷,在军列前挥手。
甚至在我的生日,宣传部门特意拍摄了一组“亲民”镜头:我在花园里亲手喂小鸟、在阳光下翻阅报纸、在工坊中与女工们交谈——
他们说这叫“皇权的人性化”。
但我知道,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神化。
把我打造成一种超越真实的存在,一种“理想中的雷瓦尼亚”本身。
不是一个会犯错的年轻女性,而是一种精神象征——
一位不知疲倦、不曾恐惧、永远坚定,永远正确的“时代引路人”。
但就像海因里希所说的那样:
“陛下仍然太像一个人,而不是神。”
在过去,我也会在自己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出现在人群面前,发表一些激昂的演说。无论是在皇都的广场上,还是前线的营地里,那些话语都带着愤怒、信念与真情实感——我希望能真正打动他们,点燃他们心中与我一样的感受。
可当海因里希翻阅了我过往的讲稿之后,他却只是沉默地合上笔记本,然后说出那句总结性的评价。
“太真实了。”他说,“陛下表达的情绪太复杂、太具体。但民众真正想听的,是他们的神话。”
我不禁皱眉:“可如果连我都不再表达真实的感受,甚至不再像个真正的人,那他们到底该信的是什么?”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给我展示了一段他们正在剪辑的新电影。
画面里是我站在那次被联合王国轰炸留下的废墟中央,手里拿着一面雷瓦尼亚旗帜。
背景是弦乐编制的慢板胜利曲,旁白在低声述说“陛下亲临废土,只为让孩子们仍能看到黎明”。
我记得那天我只是说了句“修复排水系统要紧”,根本没说这些话。
可看着这剪辑成型的影像,我竟一时无言。
“陛下明白了吗?”海因里希看着我,像是一个布景师在对主角解说舞台的光线变化。
“民众不需要一个表达真实情绪的人。他们只需要知道,就算天塌下来,陛下也不会退后半步。”
“哪怕那不是事实?”
“那就让它变成事实。”
从那天起,我的演讲稿也开始交由他来润色。
不再有太多的个人情绪,也不再有“我希望”“我想要”这样的句式。
取而代之的,是宏大、空灵、不可动摇的宣告——
“这是命运所指之路。”
“是历史选择了我们。”
“雷瓦尼亚,将成为未来的火种。”
我的每一个词句都如圣典般,被成千上万的人记录、传诵、印刷、剪辑、加上背景音乐,在课堂、战地、剧场、乃至教堂中反复播放。
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不只是靠枪炮和坦克。
它靠的,是无数人对一个虚构版本的“我”心甘情愿地信仰与服从。
所以我站上演讲台,面带微笑,目光如炬,语气坚定,声音不容置疑。
哪怕演讲结束后,我会在后台一个人坐在阴影里,脱下那件沉重的披风,捏着手中的讲稿,看着上面那些不完全是由我写下的文字。
我依旧要承认:
那些话,确实比我曾经说过的任何一句,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