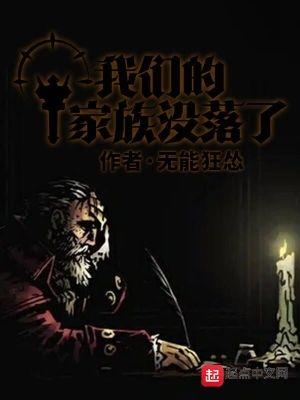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女王受 > 第262章 胜利的剧本(第1页)
第262章 胜利的剧本(第1页)
除了暗地里的那一切,维系这场战争运转的,还有另一套同样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它不像军工厂那样轰鸣,也不像后勤运输那样可量化,却在不知不觉间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那便是宣传。
或者说,“国家叙事”。
海因里希是个真正的天才。如果说阿斯塔是秩序的执行者,那么海因里希,就是这场秩序幻象的总导演。
他一手建立的“中央舆论指导委员会”如今己覆盖全国所有主要媒体——报纸、电台、剧院、学校、宗教机构,甚至连市集布告栏和火车车厢内的宣传画,也必须经过他的团队审批。
最初,我只要求他维护国内稳定,可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整的“胜利剧本”。
在这套剧本中,雷瓦尼亚是世界新秩序的曙光,是旧世界崩塌后唯一的火种;而我们现在打的每一场仗,不是为了扩张,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
他将我们塑造成“文明的捍卫者”、“秩序的守望人”,而我们的敌人——不论是联合王国、帝国、反抗军、还是过去那些叛乱的旧贵族——无一例外,都被描绘成“腐朽世界的残渣”,是“拒绝进步、背叛未来”的象征。
这种叙事手法太过成功,以至于我有时候都会被它欺骗。
“战争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重建。”这是他最常引用的一句口号。
而这种重建,当然不是从砖石开始,而是从思想开始。
海因里希的宣传部门将“进步”与“服从”紧密绑定,将“自由”与“混乱”划上等号,把“胜利”塑造成一种集体道德上的奖励,而非仅仅是战术或资源上的胜果。
只要还在胜利,民众便会相信我们是正义的。
只要还有面包与歌剧,他们便愿意无条件地信任我们。
甚至于,他们愿意主动配合国家叙事的建设。
有人写信给广播台,举报邻居在深夜收听联合王国的短波频道;
有人自发组建剧团,在占领区巡演爱国剧目;
还有小学生在作文里写下“我长大也要加入前进军,为女皇陛下扫清邪恶”。
人们似乎在宣传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安慰——哪怕他们不真正理解这场战争是怎么运作的,甚至不清楚我们到底战胜了谁、攻占了哪座城市,但只要广播里说“我们正在胜利”,他们就会安心。
而这,正是海因里希的才能。
他说:“人类可以忍受饥饿、寒冷、伤痛,却无法忍受没有意义。”
于是,他用意义将整个国家包裹了起来。
将服从包装成道德,将征用美化为奉献,将牺牲升华为荣耀,将战争渲染成史诗。
我原本担心,宣传是否太过夸张,是否会引发民众的理性反弹。
可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己经踏入战争轨道的国家里,人们其实并不渴望真相。
他们只渴望一个解释,渴望一个能让他们安睡的版本的故事。
而海因里希和他手下的人,恰好提供了这种版本的故事。
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在沉夜疲惫时,听着那一成不变的“胜利进行曲”,短暂地忘记正在进行的战争,仿佛自己真的处于一个无比繁荣的时代。
可我知道这是假象。
但是假象也能支撑国家。
如果真相会动摇一切,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用谎言来筑墙。
有时我会想,我们和那个旧时代的神权国家、暴君王朝、或是宗教审判团之间,到底有多少不同?
然后我又会想:至少我们的谎言,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是吗?
只要我们能赢,就一定是的。
而在这种叙事之中,我,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个角落。
不只是作为一个统治者,而是成为整个国家叙事的“中心象征”。
每一次战报发布会,每一次授勋仪式,每一次前线电报送抵皇宫,我都必须在镜头前微笑、鼓掌、致辞。哪怕只是几句言简意赅的鼓励,也必须经过宣传部的反复雕琢、推敲、排练,再由摄影部门选取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剪成精致的片段送往各地。
“女皇陛下与士兵共饮热汤”、“女皇亲自出席前进军凯旋典礼”、“女皇步入机械工坊勉励工人”——这些标题如今几乎成了每周固定播报的模板。
海因里希说:“一个理想的国家,需要一个真正的‘信仰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