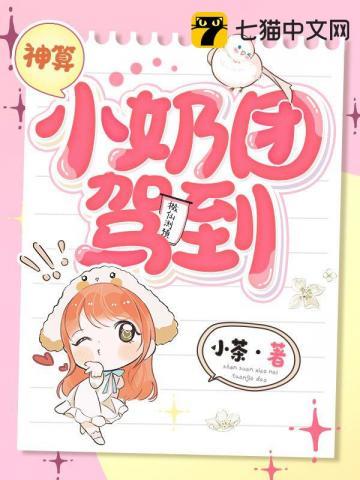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朕唐武宗开局在仇士良刀尖躺平 > 055司马懿 勿cue(第2页)
055司马懿 勿cue(第2页)
刚走出紫宸殿范围不过百步,穿过一道宫门迴廊,李炎猛地顿住脚步,抬手重重一拍额头,发出一声懊恼的轻呼道:
“哎呀,怎地把如此要紧之事给忘了。”
李炎毫不犹豫,立刻转身,带著隨从又匆匆折返回紫宸殿。
殿门再次被推开,李炎的身影重新出现。
殿內的仇士良刚在御案旁的锦墩上坐下,正展开那份批了可字的奏疏细看,闻声愕然抬头,心中疑竇丛生:
陛下怎地又回来了?难道对新规有变卦?
仇士良眼中带著讶异,连忙起身。
只见李炎脸上带著几分急切与追悔,几步走到仇士良面前,语气郑重道:
“仇公,朕方才心神不寧,竟忘了还有一件极其要紧之事,需得立刻与你商议。”
仇士良连忙躬身说道:“陛下请讲,老奴洗耳恭听。”
李炎深吸一口气,眼中流露出深切的感伤与怀念,声音也低沉柔和下来的说道:
“今日朝会散时,朕隱约听得几位臣工閒谈,提及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白冯翊,在洛阳履道里养老,又作了新诗。”
李炎顿了顿,目光似乎穿透殿宇,望向遥远的童年时光说道:
“仇公有所不知,朕的亡母生前,最是喜爱诵读白乐天的诗篇。
尤其在朕儿时,阿母常常將朕抱於膝上,揽在怀中,一首一首地念给朕听。”
李炎的声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他微微侧过脸,手指无意识地抚过衣袖后继续说道: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些句子,朕至今字字铭心,皆,阿母念诗时的神情语调,恍如昨日。”
殿內一片寂静,只有李炎低沉的敘述在迴荡,充满了对亡母刻骨的思念。
李炎猛地看向仇士良,眼神变得坚定的说道:
“如今,朕承继大统,贵为天子。
追封阿母为皇太后,身为人子,岂能不为阿母身后事尽一份心?
朕欲召白乐天回京,让这位阿母生前最喜爱的诗人,亲自为阿母撰写祭文与墓志铭,唯有他的才情与声名,才配得上阿母的贤德慈爱。
此乃朕的一片孝心,亦是对阿母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李炎的脸上出现的踌躇与忧虑,语气也带上了一丝顾虑的说道:
“只是仇公,你说朕该以何等名义召他还京?
白乐天毕竟是四朝老臣,名满天下。
若直接以撰写亡母祭文、墓誌为由徵召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是否显得朕过於苛待老臣,不恤人情?
於朕仁孝之名可有损碍?仇公久歷朝堂,以为朕当以何名义相召,方为妥当?”
仇士良静静地听著,在脑中迅速思考:
不愧是你啊陛下,重情念旧,至孝至纯,却又如此爱惜羽毛,既想用人,还怕自己名声有损,落个苛待老臣的名声。
这份心思,倒是简单好猜。
白居易此人当年在元和年间,倒是跟著裴度、武元衡他们一起积极襄助宪宗皇帝削藩,是那短暂元和中兴的鼓吹者之一。
在朝堂之上他也没少上书言事,矛头直指宫闈宦官,那首《卖炭翁》,句句如刀,讽的不就是咱这些宫使?
“罢了,”仇士良很快做了决断,心中冷笑道:
“终究是个风烛残年、半截身子入土的老朽,且已远离中枢多年,在洛阳吟风弄月,还能翻起什么浪来?
陛下此举,彰显孝道,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义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