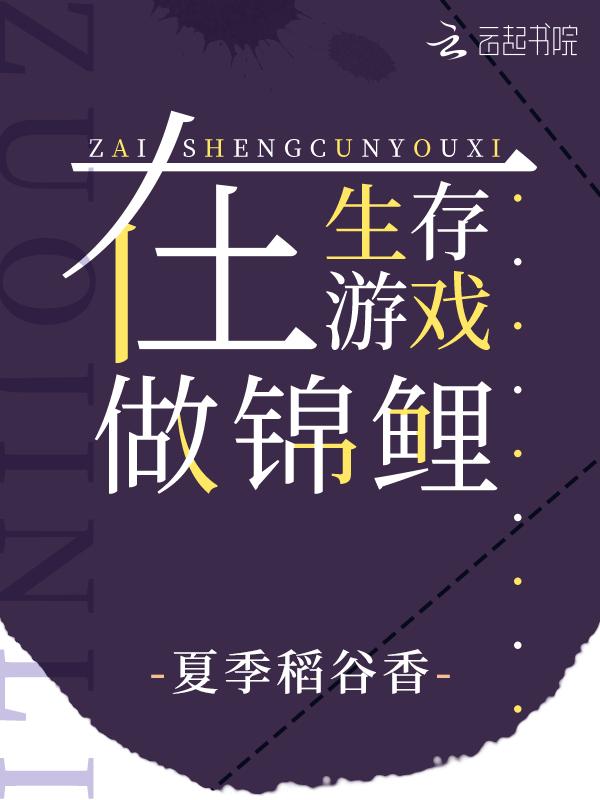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清朝流放宁古塔在哪里 > 第16章 诛杀乌兰(第2页)
第16章 诛杀乌兰(第2页)
乌兰暴喝旋身,锤链绞住刀锋溅起一串火星。两匹战马嘶鸣着人立而起,铁蹄在冰面上犁出蛛网般的裂痕。
陈嗣业突然松手弃刀,乌兰收势不及踉跄前倾,却见那汉人如鹞鹰翻身跃上马背,靴刃寒光一闪——
“嗤啦!“
乌兰肩甲应声崩裂,一道血线顺着黥面蜿蜒而下。
他狂怒地扯断锤链,将半截铁索抡成血色旋风:“只会耍弄机巧的鼠辈!“
陈嗣业飘然落回坐骑,指尖掠过腰间火药囊。
雪沫混着血珠在两人之间纷扬,他望见乌兰瞳孔中跳动的暴戾,像极了那夜在温泉洞窟斩杀的巴日卡。
“将军可知,“他突然策马斜冲,“冻蛇复苏时——”
话音未落,三支鸣镝尖啸着穿透风雪。
乌兰猛拽缰绳欲追,座下战马却突然悲鸣跪倒——冰面下不知何时渗出漆黑火油,七条浸油的麻绳正沿着陈嗣业方才的蹄印蛇行燃烧!
“轰!”
火龙腾空的刹那,陈嗣业扯下大氅抛向半空。
乌兰在烈焰中挥锤劈开布帛,却见漫天灰絮里寒芒骤现——那柄弃落的右刀竟系着天蚕丝,此刻随布帛飞舞划出致命弧线!
金瓜锤格挡已迟。
刀锋吻过咽喉时,乌兰听见那个南蛮的声音混在风雪里:“。。。因为冻蛇的血,会脏了利爪。”
镶蓝旗大纛轰然倾塌,陈嗣业立于燃烧的冰崖之上,看乌兰的尸首坠入深渊。
血珠顺着刀尖滴落,在雪地上绽出一串红梅,很快又被新雪掩去痕迹。
远处索伦部的牛角号撕开云层,像头苍狼在对月长嗥。
他拾起乌兰的狼首兜鍪,指腹抚过盔檐的霜纹,忽然想起那日博木博果尔歃血时的眼神——草原的雪永远埋不住刀光,正如鹰笛声里,永远飘着未冷的血香。
他的身后,索伦部英勇的战士们手中紧握着长刀,每一次挥砍都精准地落在了正蓝旗士兵们的身上。
尽管现在已经是开春,但是鹰钩涧的气温依旧很低,再加上先前海东青们撒下的高温铁屑,热胀冷缩作用下正蓝旗的盔甲像是薄纸一样脆弱。
“索伦部的男人们!让这群正蓝旗的看看,对你们的女人和牛羊有企图,究竟是什么下场!”
博木博果尔高声呼喊着,同时一刀砍掉了一个正蓝旗士兵的脑袋。
鲜血喷洒在空中,还有索伦部人的铁甲上,浓烈的血腥味让狼奴失去了判断,他们疯狂挣脱着束缚,遇人便咬,腥臭的口气和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混合在一起,战场上的所有人都像是着了魔一样。
他们的眼中只有劈砍,也只有劈砍能够让他们活下来。
陈嗣业不知道自己砍下了多少个正蓝旗士兵的头颅,他的脸上和铁甲上已经浸满了鲜血,手中的刀毫无章法地挥舞着,肾上腺素飙升,他甚至已经没有了对于痛觉的感知,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究竟是不是战争,如果是,他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战争是能够麻痹人的,直到这一刻陈嗣业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天空中忽然飘起了小雪,雪花落在地上的一瞬间便被血液染红。
陈嗣业将脸上冻成冰渣的血液抹掉,握着刀的手停不住地颤抖,似乎还在渴望着鲜血。